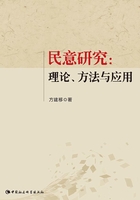
第四节 民意的另类表达
公众有多种方法对公共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投票时、在回答民调问题时,这种声音大多是直接的。当然这不是他们仅有的选择。站在与国家机器的对立面,他们既可以采取不配合、不服从等消极方式,也可以通过签署请愿书、举行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采取参与社会革命或犯罪等极端方式。人们采取这些另类的民意表达方法,大多是因为常规方法难以奏效。这些另类的民意表达与选举和民调所展示的民意往往是相冲突的。
近年来,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这对社会问题的表达诉求也日益强烈,然而民意机构与民意通道却难以满足公众的表达愿望,导致群体性事件及其他非理性表达方式的频发,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显而易见的威胁。
没有自由顺畅的利益表达或民意表达就不可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虽然理论上我们似乎从不缺乏公众表达民意、反映意见的渠道,诸如人大、政协职能的发挥,还有各类民主恳谈会以及市长信箱、市长热线等形式,但实际操作中民意表达渠道却往往未能实现真正顺畅,甚至不时出现“肠梗阻”现象。因此,公众除了通过听证会、信访以及各类民意调查等体制内的表达方式外,还不得不通过签署请愿书、集会、游行、罢工,甚至诉诸暴力的方式,对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将这类体制外的、非正式的,特别是非理性的民意表达方式称为民意的另类表达。在各类矛盾凸显的当今社会,研究另类的民意表达所蕴含的民意,并基于此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限于篇幅,本节主要讨论网络民意表达、手机短信、群体性事件等近年来比较突出的几种另类表达。
一 网络民意表达
网络民意表达既有积极促进社会发展进程的一面,也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内影响最大、势头最盛的民意平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的数量已达到6.18亿人,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是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将近3/4居住在城市地区,九成以上处于劳动力年龄段。因此,把网民整体上视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把网民整体的意见视为主流民意、把网民整体中的不同意见视为整个社会多元化的反映,是符合事实、合乎情理的。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中国普通民众在网络上发出的声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些高层官员常常通过互联网络倾听网友的意见和建议,有的官员开设的微博影响力很大。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也主要是在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进而引发广东本地媒体、中央和各地官方媒体的竞相报道,最终促成国务院宣布废除实行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同时公布惠及千百万人口的《城市生活无着者流浪乞讨人员救济管理办法》。2013年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一案更是受到了网民的广泛关注,引发了社会对终结劳教制度、构建公平正义和司法公信力的期待,并最终促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
网络流行语、网络雷词传递着老百姓的“意愿”、“诉求”和“风向”,也是民意的表达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几年都会公布年度网络流行语排行状况,如2008年排名前8位的分别是:“囧”、“被自杀”、“山寨”、“很黄很暴力”、“俯卧撑”、“雷”、“很傻很天真”、“打酱油的”。这些看似尖酸刻薄的网络流行语,其实就是社会民意的另类表达,里面蕴含了公众对社会对政府的意见和态度。
微博开启了民意表达的新方式。微博尽管出现时间不长,但用户数量处于高速上升的状态。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微博用户已达3.31亿户,较2012年底增长了2216万户。由于微博操作简单便捷、准入门槛较低,而且提供手机等多种终端登录,使其成为公众发出声音和获取信息的重要场所。微博对网民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对社会舆论和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已经充分显现,从李开复的离职声明到纷扰至今的“学历门”,从春晚后的网友回馈到日本大地震募捐争议,这些大小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话题,大多出自微博。
尽管存在网络民意表达主体(网民)分布不均以及网民发言匿名性导致的表达内容真实性存疑等问题,使得网络民意难以获得规范性民意调查那样的代表性,但即便是网民的非理性言论,也聚合着公众的某种愿望和诉求,因而具有常规民意表达所不具备的许多优势和特点。在温州购房门、云南“躲猫猫”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环保局长被邀游泳等一系列网络公共事件中,网民们的言论不仅直接推动了事件真相的调查,而且网民对事件公开讨论本身就是在践行公民权利,因为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手机短信
美国学者保罗·利文森在他的《手机》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经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如果他们被迫在书籍、广播、电视、电脑、固定电话、手机等媒介中选择留下一种,会选什么?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选择的是手机。
截至2011年8月底,我国手机用户数量已达到9.3亿,用户平均每周收到短信息34.6条,短信让内向害羞、不善言辞的中国人更爱“说话”了。当然,对中国公众而言,短信并不止于表情达意或增加人情味。当中国改革步入深层次的攻坚阶段,短信的“超能量”也随之爆发,“戏说官场”位列中国短信分类“前三名”表明,短信已成为一种全新的民意表达路径。2007年被中国传媒界视为短信力量的“释放年”。这一年,一则群发短信激起了厦门PX(对二甲苯)事件“千层浪”。从2007年5月下旬开始,厦门百万市民互相转发一条关于PX危害性的短信。一条短信演变为“百万短信”,进而在社会底部自动凝聚起一股强大的民意,最终实现下情上达。尽管厦门事件具有其特殊性,但短信已跃升成为一种不可漠视、必须对其有所敬畏的民意载体。
其实,短信作为民意表达的路径,早在2005年3月的黎巴嫩就已充分展现其威力。在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一个月之际,以手机短信作为主要传播方式之一,只有400万人的黎巴嫩爆发了8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把整个国家1/5的民众推上街头进行抗议。
人不但是一个自然人,而且是一个社会人,人作为社会中的活动主体,无不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趋同心理和自我表现欲望是短信作为民意表达重要方式存在的社会心理土壤。腾讯公司2011年初推出的微信,功能更加丰富,使用更加便捷,已成为公众相互交流、表达民意的重要载体。
三 群体性事件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德文版的《风险社会:走向另一种现代性》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并认为现代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之中。近年来,我国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处于多发态势。据中国社科院主编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年到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另据《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披露,2007年全国各类群体性事件已上升到8万余起。近两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仍在逐年上升,其中突发性群体事件所占比例以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群体性事件反映了当前我国民意表达不畅的现实困境。以比较温和的出租车司机罢运来说,据《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9月26日的报道,近7年来共发生了数量超过百起的集体“停运”事件。由于油价不断上涨、道路日益拥堵等,每天工作时间常常超过12小时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却在逐年下降,集体停运成为每个城市出租车司机多次向运管部门反映无果后的无奈选择。
2011年底发生在彭湃烈士故乡广东陆丰的乌坎事件表明,自9月份以来,部分村民之所以频频上访,缘于对村干部处置土地、财务、换届等问题的不满。如果能认真倾听民意,及时抓住利益诉求点,直面并解决突显的矛盾和问题,就不会小事拖大、层层升级,演变成群体性冲突。以广东省委副书记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也正是因为能够以“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才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
始于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活动,尽管与出租车罢运等群体性事件有很大的区别,但其通过和平静坐等形式表达对金融制度偏袒权贵的不满,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以另类的方式表达公众或相关利益群体对政府和社会的诉求,各类口号、标语、请愿书、倡议书等等,都是他们民意的表达。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即心怀不满的民众即便保持沉默也仍可能以各种方式“用脚投票”,如移民海外、向国外转移资产、抵制向红会捐款、不行使选举权、藐视他们不赞成的法律法规等等。但是,除非这些不满转化为集体的行动,否则以上任何一种另类表达都不足以引起政府的重视。尽管如此,上述表达方式都蕴含着公民支持与反对的信号,包括:什么是他们可能忍受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承担作为公民的义务,他们在多大范围内支持或不支持他们的政府及其政策。所有政权包括专制政权的合法性,最终都取决于民众的意志(Hume,1752/1906,pp.243ff.)。
在那些禁止民调的国家里,另类表达依然是了解民意的不可或缺的信息源。即便在许多民调得以广泛利用的国家,在反映那些未被作为民调议题的某些群体内搅动的暗流时,抗议事件也常常比民调数据更有用。李(Lee,2002)通过对有关种族问题的民调跟美国民权运动的相关性进行考察后发现,某一年民权运动引发事件的数量跟次年民调中的种族态度问题有着清晰的相关性(p.89)。尽管民调常常滞后,但监控这类事件往往能够加强我们对民意的理解,即民意在形成之前受到哪些力量的影响。
四 时尚文化
时尚传播和时尚文化是考察民意的风向标之一。文化研究学者对公众如何运用大众传媒的符号世界以及通过对时尚文化的吸纳、消费或拒绝、抵制来表达观点和态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时尚文化由于受到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影响,在主流社会和主流教育中起着导向的作用,由此促进人们对社会规范的遵从。
音乐和时装看起来都是“好玩”的东西,因此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在增进社会凝聚力、制造社会等级标记方面的作用,及其迫使人们遵从的“纪律惩戒力量”(Noelle-Neumann,1984,p.117)。男孩乐队、Hip Hop、校服、着装标准,都被用于区分年轻人与老年人、男人与女人,区分不同社会等级、职业、态度、价值观和信仰。音乐和时装是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和社会整合手段,如果哪个个体被认为在时装或音乐方面落伍,就可能面临被排斥和孤立的恐惧,其能量不容忽视。音乐和时装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手段,它们既是功能性的(可听、可穿),是传播和政治陈述的形式,也是社会遵从的工具、思想表达的机制和社会抗拒的武器。
文化研究理论指出,受众或消费者对喜欢和不喜欢的表达,不仅反映在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欲望,而且反映在制造商想要他们建立的价值取向和欲望。因此,作为声音的音乐和作为衣服的时装,既可以是一种偏离界限确认的行为,也可以是文化区隔的破坏者。作为一种物质的、商业的、传播的现象,作为一种政治工具,音乐和时装既可建构也可解除个人身份上的界限。由此可见,作为传播的音乐和时装既是对消费者的隐匿,又制造了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距离,而企业则可从连续不断的时装周期中获益。作为产业的音乐和时装涉及各方面经济利益的融合,包括制造商、广告商、评论员、批发商、模特和杂志,这是一个“结构上相互依赖的经济利益体以利润为驱动的联盟”(Davis,1992,p.12)。最后,作为思想观念的音乐和时装,通过对群体间各种区隔的建构、强化、主流化,起着再生产的作用,而不管这些区隔是基于种族、性偏向、性别还是阶层。
然而,要测量音乐和时装承载的民意,并非那么容易。大多数报告依赖于业内人士发布的销售数字和年度报告,我们无从知晓人们对自己所买和所不买的音乐和时装持什么态度。对很多民意研究者来说,这两大行业被视为不足道的、娱乐性的甚至“好玩的”。然而,这些挑战为研究者提供了机会,他们希望考察这些作为民意表达方式的喜欢与不喜欢和遵从与反叛。今后的研究,可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多层次的分析,考察各种各样的流行文化形式背后所隐藏的企业、内容和受众,以进一步了解流行民意的文化表达、经济表达和政治表达。
[1] James Reston,1909—1995年,美国著名记者,曾任职于美联社、纽约时报社,1961年荣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1991年荣获四大自由奖,被誉为“美利坚的良知”、“继李普曼之后最卓越的新闻人”等,著有回忆录《截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