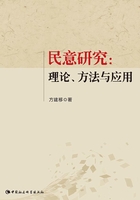
前言
Public Opinion“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最恒久的词”(Price,V.,1992),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跨学科性质的术语之一。对政治学研究而言,它是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可用以检验政府的政治决策是否反映公众意愿。对历史学家来说,它是理解社会变迁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发展或演变方式的因子之一。社会心理学家则将之视为影响公共领域中个体行为的一种力量,以及作为不确定情境中决策的一种辅助(Hofstätter,1971)。而法学研究者感兴趣的是,立法和司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民意的变化。Public Opinion也是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规范执行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许多社会学家将之作为“大众社会”中具有威胁性质的一种现象进行研究。传播学者则将大众媒体看作了解公众所思所想的信源之一,并通过研究大众媒体对民意的影响,用以描述民意并解释民意的变迁。
Public Opinion一词在汉语中有多个对应的“称呼”,如民意、舆论、舆情、群意等,但这些“称呼”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内涵差异。有研究者(王来华、林竹、毕宏音,2004)认为,舆情与民意在概念上的相似性更强,而跟舆论在概念上的相似性较弱。舆情和民意都包括公开与不公开的“民众意见”,但不一定是媒体上的信息,也不一定完全依赖媒体上所呈现的思想或观点。舆论则从了解公开的意见出发,更加倚重各类媒体中表达的信息,也更加强调大众传媒与舆论之间的关系。国内研究者似乎更偏爱“舆情”这个词,但本书不打算“从众”,倾向于使用“民意”一词。这主要基于几点考虑:第一,民意这一概念外延更宽泛,它不仅包含媒体上公开的意见,而且包括那些未经公开但又可通过科学方法测量的“沉默的声音”;第二,舆情蕴含着“有情况”之意,在现有语境中,它常常跟“应对”联系在一起,让人觉得舆情就是指那些不期而至的、令人棘手的情况;第三,采用民意一词有利于跟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各方学者进行学术沟通,有利于在“世界民意研究会”这类行业框架中进行业务交流。
有两项技术改变了现代政治体制,这就是电视和民意研究。电视将政治普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它已取代传统的政治体制而成为权力的中心。运用现代调查技术进行民意研究,似乎已成为民主国家政治决策的基础。电视以及今天已经普及的互联网,跟民意研究一道,已经成为当今政治选举、公共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人对民意调查提出质疑:从总体中所抽取的样本所获得的数据跟民主理论研究者的经验是否存在关联?用样本所测量的多数人的民意存在多少的“理性”?我们是否能够或者必须避免公民受到所发表的民调数据的影响?更何况,民意不一定等同于民调数字所展示的内容,因为公众除了在投票时、在回答民调问题时发出自己的声音外,还可以通过签署请愿书,举行罢工、集会、游行、示威,采取不配合、不服从,甚至采取参与社会革命或犯罪等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现代民意研究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现代调查技术的出现,它是在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滋养下,得以逐步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自1935年盖洛普创建美国民意研究所以来,民意调查在抽样方法、访问方式、误差控制、理论阐释等方面均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计算机辅助面访、计算机辅助自主访问、计算机辅助网络调查系统相继得到应用。调查方法的科学规范为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然而,民意研究不仅仅是民意调查,民意调查也不仅仅是定量的调查。近年来,在线调查、协商性民调、网络语义搜索与分析等新方法的诞生与应用,进一步促进了民意研究行业的发展。
民意调查应用广泛。在西方国家,自科学的民意调查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运用联系在一起。如今,民意调查除了用于政治选举外,还广泛应用于调查人们对某项政策、某种产品、某个事件以及社会福利、环境污染、种族偏见、吸毒现象等问题的态度。
在中国大陆,民意调查日益受到重视,但在调查机构、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结果使用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虽然近年来有关民意调查的著作和论文增长很快,但从内容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舆情研究多,民意研究少;网络民意研究多,科学民调研究少;民意解读研究多,民调方法研究少。可以说,民意研究还没有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发挥应有的作用。近年来围绕PX项目、垃圾处理、城市管理等议题进行公共决策时所呈现的“沉默立项开始,聚众反对叫停”[1],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要走出这一怪圈,必须重视民意研究,及时把握公众的立场和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社会沟通和舆论引导。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降低政策执行的成本,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在媒介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公民参与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政府和公共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将民意研究狭义化地理解为舆情应对,将舆论引导简单化地等同于突发事件、负面事件处理中的信息屏蔽或发布,这样的思维或行为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必将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
本书将民意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分析阐述,旨在使读者对之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解,并能运用书中的相关方法开展民意研究。本书既有相关的概念辨析,也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既介绍民意调查的经典方法,也介绍近年来民意研究方法的新发展;既包括民意形成与发展的理论,也包括民意调查在一些主要领域的应用。希望本书的出版对于民意调查的实施者选择合适的调查方法、规避相关的错误和误差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对民意研究者的理论创新、民调选题的价值导向和民调方法的科学规范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书由六个部分组成,共计十九章,外加一则附录。
第一部分:民意及民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包括两章内容。
第一章“民意的本质与表现”,主要阐述民意与民调的关系,民意的表达途径以及社会精英的“民意”;
第二章“民意调查的历史与现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民意调查的历史与现状、欧美国家政府对民意调查的运用,以及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民意调查的发展状况。
第二部分:民意研究的主要理论,包括四章内容。
第三章以心理学为视角阐述民意的形成与改变,主要介绍态度的结构、态度形成与改变、态度的测量,以及知识、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第四—六章以传播学为视角阐述与民意形成密切相关的三个理论,即沉默的螺旋、两级传播和议程设置。
第三部分:民意调查抽样与设计,包括三章内容。
第七章阐述抽样的目的、概念、方法和步骤;
第八章介绍问卷的结构与类型、问卷设计的步骤与注意事项,以及问卷质量的评估;
第九章阐述检验问卷设计质量的两大指标——信度与效度,以及信度与效度的关系。
第四部分:民意研究具体方法,包括四章内容。除了阐述电话调查、自填问卷调查、访问调查等常用的传统民调方法外,还添加了一章内容分析,因为民意研究不仅仅是民意调查,对现有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媒体报道内容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探究民意变化的轨迹和深层次因素。
第五部分:民意研究方法的新发展,包括三章内容。民意研究不仅仅是定量的调查,也包括定性的分析。该部分除介绍近年来运用较广但颇受争议的在线调查外,还设专章阐述仍处于探索与试验阶段的协商性民调(DP),以及这几年兴起的网络语义搜索与分析方法。
第六部分:民意研究的运用,包括三章内容。分别从政治选举、公共政策、新闻报道三个方面介绍民意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以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附录:世界民意研究会(WAPOR)专业守则。为推动民意调查的科学应用及履行机构的公众责任,世界民意研究会专门制定会员专业守则,要求其成员恪守,以维护公众的信心,保护公众免受鱼目混珠的“研究”的误导或利用。最新版的专业守则自2011年12月1日起生效。
这本书从构思到完成费时整整三年。三年来,我时时鞭策自己,提醒自己不能懈怠。“久孕不育”是一种煎熬,但随着资料的日益丰富,写作思路的日益清晰,写就的初稿日益丰厚,就像孕妇看着日渐隆起的肚子,成就感也越来越强烈。在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几位友人的协助:崔波博士、孟慧丽博士和黄宏讲师分别撰写了第十五章(协商民意调查)、第五章(二级传播)、第十四章(在线调查),上海易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克旭博士撰写了第十六章(网络舆情监测与语义分析),浙江传媒学院管理学院葛进平教授和复旦大学在读硕士生马剑通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诸多意见,在此谨表深深的谢意。
近年来,本人一直致力于受众心理和民意调查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通过学术会议等平台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交流,受益匪浅。2012年,本人申请的“公共决策与舆情研究实践基地”获得了浙江省提升地方高校办学水平专项资金的资助,这为民意研究服务于公共决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一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我们所完成的舆情研究报告的肯定成为我们进一步要求自己、提升研究水平的动力。2014年所中标的杭州市决策咨询委招标课题《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决策的社会沟通协商和舆情应对机制研究》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将民意研究服务于公共决策的决心。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在此诚恳地请各位同行和读者提出批评,给予指正。
[1] 参见2014年5月12日央视新闻频道节目《新闻1+1》:《“城市垃圾”为何变成“情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