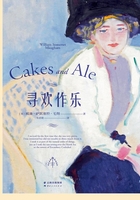
第一章
时常会有人打电话找不到你,留言央你一回来就打给他,说有要事相商。我注意到但凡如此,事情往往对他来说比对你更紧要。如有礼相赠或对你有什么其他好处,多数人都还能耐着性子适度等待一段时间。所以当我回到住所,听房东太太费洛斯小姐说阿尔罗伊·基尔先生希望我立刻给他打电话时,我觉得暂不理会也没什么关系。我的时间刚够喝上一杯、吸支烟、看份报,之后便要穿戴整齐出去吃饭了。
“是那位作家吧?”她问我。
“是的。”
她不无友善地瞥了电话一眼。
“需要我拨通他么?”
“不用,谢谢你。”
“他要是再来电我该怎么说?”
“请他留言。”
“那好吧,先生。”
她噘起嘴,拿着空苏打水瓶,扫了一眼房间,觉得还算整洁,便走了出去。费洛斯小姐是小说迷,罗伊的书她肯定都读过。我的漫不经心让她很反感,这表明她是很欣赏罗伊的。再到家时我发现她在餐具柜上留了张便条,字迹粗大,很容易辨认:
基尔先生打过两次电话,问您明天能和他共进午餐吗?如不能,那哪天合适?
我挑挑眉。我有三个月没见到罗伊了,而上次也只是在聚会上聊了几分钟。他极为友善,一向如此,分别时他还表达了碰面太少的由衷遗憾。
“伦敦真是糟糕,”他说,“总是没时间见想见的人。下周找机会一起吃午饭吧,好吗?”
“我很乐意啊。”我答道。
“我到家后查一查本子,给你电话。”
“好的。”
我认识罗伊二十年了,当然听说过他那个小本子,总是放在马甲左上方的口袋里,记着各类约会,所以之后就没了音信我也不感意外。眼下我也很难相信他这么急切殷勤地要招待我是平白无故的。临睡前我一边抽烟斗一边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思索,罗伊找我吃午饭会有哪些原因。或许是他的一个崇拜者缠着他要把我介绍给她,或是一位曾在伦敦逗留了几天的美国编辑希望罗伊牵个线。可我不能把老朋友想成连应付这种局面的手段都没有,如此猜度可不厚道。况且他说过由我挑日子,不太可能是要我另见什么人。
没有谁能像罗伊这么真挚友善地对待一个口碑甚好的同行小说家,可当后者陷入怠惰、失意或被别人的成功抢了风头时,罗伊的背弃也是最痛快的。爬格子的总是起起伏伏,一淡出公众视线我就特别有体会。显然找个婉拒的理由可能也无伤大雅,尽管他是个很有决断的人,要是打定主意了要见我,我很清楚就算直截了当地说声“滚你的”也阻挡不了他的执着,不过我已有了好奇心,再说我也挺喜欢罗伊。
我曾不无钦佩地目睹他在写作界声名鹊起。对于任何一个文学青年来说,他都是个励志楷模。我想不出同代人中还有谁能以这么平庸的资质取得这么显赫的地位。如同聪明人日服一剂“比麦斯”胚芽乳,他靠的大概也是“每天一满勺”这样的积累。他很清楚自己的本事,已出的三十来本书有时于他而言不啻为奇迹。查尔斯·狄更斯在一次餐后演说中谈到,天才便是集苦功之大成。我不禁想到罗伊初读此演讲稿时一定有灵光乍现,并反复琢磨着。果真如此,他准是告诉自己说,他也能够像别人那样成为天才;而当一家妇女报纸登出热情洋溢的书评并用上了这个字眼儿时(随着评论界对他的追捧,对该词使用也日渐频繁),他必是满意地长舒一口气,就像经过数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做出了填字游戏。他连年勤耕不辍,任何一个见证者都无法否认,天才于他毕竟是实至名归的。
罗伊在起步阶段还是有些优势的。他是公务员的独生子,父亲在香港干了多年辅政司后,终于官至牙买加总督。翻翻那密密麻麻的《名人录》,可以找到:“独生子,其父为雷蒙德·基尔,圣米迦勒和圣乔治高级勋爵、皇家维多利亚勋章高级爵士(见本条目);其母为艾米莉,已故不列颠印度陆军少将珀西·坎珀当之幼女。”他在温彻斯特读的书,之后上了牛津大学新学院。他做过学生会主席,若非不幸染上麻疹,多半是可以穿蓝衫征战划船赛的[1]。他的学习成绩虽不惊艳但可圈可点,毕业离校时没有一分欠款。罗伊甚至在那时就厉行节俭,不为无益的开销所动。他还是个孝子,深知父母为他支付这么昂贵的学费,是很大的奉献。他父亲已经退休,低调而讲究的宅邸靠近格洛斯特郡的斯特劳德,但他也时常去伦敦出席与自己管辖过的殖民事务有联系的官方晚宴,逢此场合他就习惯去一下雅典娜文学社,他是那儿的会员。正是通过俱乐部里的密友他才为从牛津毕业的儿子谋到了差事,为一位政治家做私人秘书。这位老爷曾在两届保守党政府里做国务大臣,备受愚弄后终于修成正果得到了贵族爵位。这使得罗伊年纪轻轻便有机会见识大世面,而他也利用得很好。有些人对上层社会的认知仅限于报刊的插画页里,其创作的形象其实已打了折扣,而在他的作品中绝不会有此类谬误。他深谙公爵们的谈话风度,对议员、律师、书商和贴身男仆的描述都恰到好处。他早期小说多用轻快的笔调刻画总督、大使、首相、皇室成员和贵妇人,其中不无引人入胜之处。他笔调友善但不屈尊俯就,亲切而非狎浪轻慢。他总在提醒你这些人物所属的阶级,但又能令你与他一同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他们和你我一样也是性情中人。罗伊对潮流走向总是把握精准。时过境迁,贵族活动不再适合做严肃小说的主题,他就将写作集中于律师、注册会计师以及产品经纪人的内心冲突,对此我总觉是件憾事。他在这些个圈子里游走时,并不像过去那样得心应手。
他辞去秘书工作专事文学后不久,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不穿鞋就有六英尺的身躯玉树临风,肩宽体健,神采自如。他不算俊秀,但自有一种宜人的阳刚之美:湛蓝而率直的大眼睛,浅棕色鬈发,鼻梁略短而阔,下巴方正,显得诚实、利落、健康。他很有运动员素养,早年作品中多有与猎犬一同驰骋的记述,文字的生动和准确让读者毫不怀疑那一定是亲历过的;直至近来他仍时常乐于弃案牍一日而寻迹山林。在他第一部小说问世的年代,作家们热衷啤酒、板球,以标榜孔武,有很多年作家板球队里总少不了他的名字。如今不知何故,这个小圈子已锐气不再,所著作品也几乎无人问津,虽说板球手的名头尚存,但在文坛却已很难立足。罗伊多年前就放下了板球,而对红葡萄酒的品鉴却颇有心得起来。
罗伊对自己的处女作并不大事宣扬。故事写得短而隽永,且趣味高雅,一如他此后的每一部作品。他把书寄给当时所有的大作家,随书奉上的信也写得让人很舒服,说他如何对该作家的作品推崇备至,如何从研读中收获良多,如何热切地希望追寻其开拓的路径,尽管还远远落在后面。他只是把自己的书呈于艺术巨匠的足下,作为一个初窥文界的年轻人向作为自己宗师级别的前辈的致敬。他称,非常明白自己的唐突,对方百忙之中还要费心于一位初学者微不足道的努力,但同时恳求对方批评指正。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少有回信只敷衍一番的。收到信的作家们对他的恭维大感受用,回复时也并不吝惜笔墨。他们推荐了他的书,有好些还邀他共进午餐。他们很难不为他的坦诚所吸引,被他的热忱所感动。他求教时所表现的谦逊打动了他们,他还表示要依循前辈的建议,真诚的态度也使人印象至深。他们感到这个后辈是值得费些功夫调教的。
他的小说大获成功,这使他在文学圈里结交了不少朋友。一时间,若是光顾布鲁姆斯伯里、肯普登山或是威斯敏斯特一带的茶会,总能见到他在递黄油面包或为老夫人斟茶。他那么年轻、那么爽朗、那么快乐,别人打趣儿时他笑得那么开心,着实很难不喜欢他。他还出入通常在维多利亚街或霍尔本一带的旅馆地下室里举行的晚餐会,那儿有作家、青年律师以及穿着“自由百货”[2]丝质衣裳、披串戴珠的女士,他们吃着三英镑六便士的晚餐,谈论着艺术与文学。人们很快发现他对餐后演说很有些天赋,又讨人喜欢,连他那世家子弟的身份也得到了笔界同辈包括竞争对手的谅解。对于他们的发轫之作他从不吝惜夸奖,当他们寄来手稿请他指教时,他也总是批阅得恰如其分。他们觉得他不仅写作功底好,而且懂得鉴赏。
他写了第二部小说,下了很大功夫,也颇得益于前辈文匠的指点。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不止一位名家为报刊写了书评,而编辑又是罗伊找过的,于是评论界自然一片赞声。他的第二部小说可以说是成功的,但还没有成功到让竞争对手们郁郁寡欢的地步。事实上,这反倒坚定了他们的想法:他永远也不会搞出惊天动地的事来。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从不选边站队。对于这么一个爬再高也不会碍事的人,他们乐得帮他一把。我就知道其中一些人,每每想起当年走错的这步棋便流露出苦笑。
不过要说他现在很自命不凡那也不对,罗伊始终保留着早年的制胜法宝——谦逊。
“我自知算不上什么大作家,”他会对你说,“跟那些文豪相比我简直就不存在。过去我还想过有朝一日要写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可是我早就连这个念想都没了,只求人们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从不放过任何草率的文字。我自认为能够说好故事,能创造活生生的人物。毕竟布丁好坏,要尝了才知道。《针眼》在英国卖了三万五千册,在美国卖了八万,下一部书我也得到了目前为止最高的连载权益。”
除谦逊之外,还有什么至今仍让他频频致信书评家,感谢他们的褒扬,还请他们吃午饭?还真没有。在如此盛名之下,当有人言辞尖锐,而他不得不忍受恶毒攻击时,他不会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耸耸肩,心里暗骂一声那个讨厌我们作品的无赖,然后就抛到脑后去。他的做法是给评论家去一封长信,说很遗憾对方把他的书批得一无是处,不过评论本身很有意思,斗胆说表现了很强的批评意识,语感也十分到位,让他觉得有必要写这封信。谁也不会像他这么渴望自我提升,并希望自己还有学习能力。他本不想告扰,不过该评论家若周三或周五无事,是否愿拨冗来“萨沃伊”吃顿午饭,并赐告究竟缘何给他的书如此差评?罗伊点午餐比谁都精通,于是一般来说,等评论家切了一大块羔羊脊肉、咽下半打生蚝的时候,也就咽下了自己说过的话。善有善报,罗伊下一部小说面世时,评论家自然会看出来,新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生活中的种种为难之一,便是如何应对那些曾经亲密无间,又随时日逐渐对自己失去兴趣的人。假如双方都过得不温不火,那关系就无疾而终了,彼此也不会记恨;可若一方名声显赫起来,情况就变得比较尴尬。交了一大帮新朋,旧友却还不好打发。他的活动应接不暇,但老友们都觉得应该把自己放在首位,他就应该唯命是从随叫随到,否则他们便会耸耸肩叹道:
“啊,好吧,我看你也不能免俗嘛。你发达了,就该让我滚蛋了。”
如果有勇气他当然就想这么干,可多数时候他没这个勇气。他软弱地接下周日晚饭的邀约。冷冰冰的烤牛肉产自澳洲,还是中午烧过了头的,至于那勃艮第红酒——哎,他们怎么会把那玩意儿叫作勃艮第?难道他们没去过伯恩[3],没在“邮政酒店”待过么?谈起当年你们挤在阁楼里同啃一块面包皮的日子,那自然充满豪情,可想到现在所居离那阁楼还那么凑近,又有些心神不宁。你的朋友说起他的书卖不出去,他的短篇小说找不到地方出版,他的本子剧院老板看都不看,而当他拿自己的作品和现在上演的一些剧目进行对比时(此时他会嗔怪地盯着你),那滋味的确不好受。你感到难堪,目光移开去。你言过其实地大谈曾受过多少挫折,好让他明白生活对你来说同样也充满了艰辛。你用最满不在乎的姿态提及自己的大作,却若有所失地发觉这位做东的故友并没有表示异议。你说起公众的喜怒无常,如此你的风头也是暂时的,这多少能让他感到安慰。他却充作了友好而严厉的批评家。
“我没读过你的新作,”他说,“不过我读了之前的一本,书名忘记了。”
你告诉了他。
“当时我相当失望,觉得不如你某些作品。当然,你知道哪一本是我最喜欢的。”
而除他外,你还受够了其他人的口诛笔伐,于是脱口说出了你的处女作。那时你二十岁,笔法粗粝质朴,每一页都满满地写着生涩。
“你再也写不出那么出色的东西了,”他热忱地说,说得你感到整个笔耕生涯自一个辉煌的开始之后便是漫漫衰败路,“我总觉得你始终没有把你显露的潜能发挥到位。”
烧煤的取暖炉炙烤着脚,手却是冰凉的。你偷偷瞄了一眼手表,心想要是十点就告辞,会不会唐突了老朋友。你已吩咐过司机等在街角,这样车不会堂皇地出现在门口而公然羞辱他的寒碜,可到了门口他说:
“马路走到底有公共汽车,我陪你过去。”
一阵惊慌之下,你招认自己是有车的。他觉得让司机等在街角很是蹊跷。你回答说司机有此怪癖。走到了车旁边,他带着宽容的优越感打量着。你不安地说改天请他吃晚饭,还答应写信给他。车开动了你还在琢磨,假如让他到“克拉里奇”赴宴,会不会觉得你太显摆,而倘若你提议在苏豪区请客,他又要嫌你小气。
这些苦头罗伊·基尔都没吃过。说得粗暴些,他尽取所得后就丢开了他们。这事要做得得体则需假以时日:辞令或暗示或润饰,口气或真心或假意,言指或嬉戏或温柔,于是虽说看穿了就这么回事,想来也只好作罢。我们大多数人在对谁做了不光彩的事时,往往对这个人也会心生厌恶,但一向光明正大的罗伊可不会有这么狭窄的心胸。无论对谁利用得有多不体面,事后也不会对这人生出半点儿恶意。
“可怜的老史密斯,”他会说,“人挺好的,我很喜欢他。真遗憾他变得这么刻薄。希望能有人为他做点儿什么。不,我很多年没见他了。过去的友谊留也留不住,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总会有谁在一群人中脱颖而出,这是实情,只能面对现实。”
但要是他在某聚会上正巧撞见了史密斯,比如在皇家艺术学会的预展上,那没有谁会比他表现得更亲热了。他紧握住他的手,诉说相逢的喜悦。他满面春风,如阳光普照一般挥洒着友善。史密斯也欣然接受了他的美意,而罗伊更是不失风度地称,自己要是能写到史密斯新书的一半好,那什么都可以豁出去。换个场面,如果罗伊以为史密斯没有看见他,他也就侧目旁顾;但史密斯偏偏看见了,便很怨恨受到这样的冷落。史密斯尖酸得很。他说在过去,罗伊乐得找一家寒酸的馆子和他分享一块牛排,也愿意到圣埃夫斯的小渔村去度一整月的假。史密斯说罗伊趋炎附势,就是个势利小人,一个骗子。
史密斯此言差矣。阿尔罗伊·基尔性格中最大的闪光点正在于真诚。没有哪个人能二十五年如一日做骗子的。虚伪这一恶习,其实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最费心费力的,得保持不懈的警醒以及精神上罕见的超脱。这和出轨或贪食还不一样,不是捞一把就走,而是全天候的。虚伪还要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幽默;尽管罗伊谈笑风生,但我觉得他绝没有那种敏捷的幽默感,肯定他也缺少玩世不恭的气质。虽然他的小说我没有多少是读完的,可开了头的却有好几本,印象中他洋洋洒洒的千篇万卷中,每一页都印着真诚二字,这也是他长盛不衰的主要根据。罗伊真诚地相信着同时代其他所有人的观念。在他写贵族生活时,他真诚地相信那都是些邪淫放荡的酒色之辈,却也不失某种贵气以及统治大英帝国的内在才干;当后来写中产阶级时,他又真诚地相信他们才是国家的脊梁。他笔下的坏人总归是坏人,好人一直是好人,少女则永远纯洁。
罗伊约奉迎他的评论家吃午饭,那是由于他真诚地感谢他的好评;而邀请不看好他的人,则是要真诚地希望提升自己。若有不知名的仰慕者自得克萨斯或西澳大利亚来伦敦,他会带他们去国家美术馆,这不仅为了树立自己的公众形象,还出于一份真诚,因为他真切地想见到他们对艺术的反应。只要去听听他的演说,你就会对他的真诚深信不疑。
他站在讲台上,身着得体的晚礼服,或者看场合需要就只穿便服,虽然很旧了但剪裁得极合身。他严肃且坦率地面向听众,表现出一种很专注的羞怯感,那只会让你觉得,他正以全然的热忱奉献着自己。他间或装出一时词穷,但随即的补说却增色不少。他的音质饱满而阳刚。他善于讲故事,不让人感到乏味。他喜欢讲述英美年轻一代作家,热情洋溢地向听众解说他们的长处,也见证了他的宽宏大度。或许他说得太多了,听过讲座之后会感觉其实已经知道了一切想知道的,再去读他们的书已是冗余。我猜罗伊在外地小城做完演说时,所提到的作家作品便无人问津了,倒是他自己的书热卖了起来。他精力过人,不但到美国成功进行了巡回演讲,在英国也同样走南闯北。没有哪家俱乐部小不起眼,没有什么协会成员的进修要求不值一提,罗伊从不怠慢,一个钟头的时间总会给足。他还不时地修订讲稿并做成短小精悍的小册子发行出版。对此类话题感兴趣的人大多至少翻阅过《现代小说家》《俄国小说》以及《有些作家》等;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些小书展现了罗伊对文学的真情实感以及讨人喜欢的个性。
然而他的活动可不止于此。他还参加各种旨在推进作家利益的组织,或积极参与改善他们因病因老致贫的潦倒境况。每当版权问题进入了司法程序,他总乐意伸出援助之手,他也时刻准备着出使国外,承担起促进建立各国作家间友好关系的重任。在公共晚宴上,由他来代表文学界作答一定会很靠谱;而若要组织委员会来妥善迎接某海外文学名流,也总是少不了他。签售义卖会上他的书至少有一种。他从不谢绝访谈,也很公允地称自己最了解爬格子的艰辛,要是愉快地聊聊天就能帮苦苦打拼的记者多挣几个钱,他是不会残忍拒绝的。通常他会请采访记者吃午饭,无不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定的唯一规矩便是文章发出来之前要让他先过目。总有人为了迎合报纸读者,不识相地打电话给知名人士,问他们是否信仰上帝,或者早饭吃什么,而对这些人他从不会表现得不耐烦。他现身所有的学术研讨会,公众都知道他对一系列问题的见解:禁酒、素食主义、爵士乐、大蒜头、锻炼、婚姻、政治以及妇女在家的地位。
他对婚姻的看法很空泛,因为在有那么多搞艺术的人遏制不住对欲望的孜孜追求时,他却能置身事外。众所周知他曾热烈而无望地爱过一位有身份的已婚女士,虽然他很有骑士风度,提到她时总不乏溢美之词,但人们也很明白她待他却是相当鄙薄的。他中期的小说因饱含辛酸而折射出这段情感苦旅。他所遭遇的精神痛楚使他能够得体地避开声名狼藉的贵妇的追逐,她们在狂热的情场里韶华渐逝,巴不得用这变幻莫测的当下来换取与成功作家的安定姻缘。当他在她们亮丽的眼眸里看到了婚姻登记处的阴影时,便坦言相告说,对早年一段挚爱的记忆,使他再无法另择佳偶偕老。他那堂吉诃德式的行为可以惹怒她们,但并不会令她们感到被轻慢。他喟叹道,这辈子是享不到安居家园之乐、含饴弄孙之欢了,不过这种牺牲是他准备好要付出的,不仅为自己的理想,也为与他同在的伙伴们。他发现人们确实很不喜欢受到作家及画家的太太们的打扰。如果艺术家走到哪里都带着夫人,那只会讨人嫌,实际上最终他想去哪儿都得不到欢迎;而如果把妻子留在家里,那他回来时又要面对指责,这又要打破潜心创作所必需的清净。阿尔罗伊·基尔是单身汉,如今年届五十了,很可能还会维持着独身。
一个作家能够做什么,并且通过勤奋、通情、诚实以及手段与目的的高效结合所能够企及什么高度,他在这些方面都是个表率。他是个好人,只有冥顽刻薄的评论家才会嫉恨他的成功。我感到临睡时心想着他的好形象会给我带来一晚的安眠。我给费洛斯小姐写了便条,敲掉烟斗里的灰烬,关掉客厅的灯便上床睡觉了。
[1]在著名的牛津/剑桥划船运动传统中,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均见两队桨手身着蓝衫出战,即文中的rowing blue,其中牛津赛服为深蓝色,剑桥为浅蓝色。
[2]“自由百货”:Liberty,伦敦西区一家高档女装百货商店。
[3]伯恩:Beaune,法国东部城市,在勃艮第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