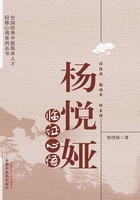
读《黄帝内经素问》引五脏病机在临床运用实录
《素问·至真要大论》归纳的病机十九条,几千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临床医生的辨证施治,是辨证求因、审因施治的准则。笔者学习其中的五脏病机,引入到临床应用,颇有收效。
一、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临证凡见头晕目眩、震颤动摇、抽搐或症状倏来倏逝者,皆为内风所致,病机所及之脏多属于肝。肝藏血,开窍于目,主筋,风气通于肝,肝为体阴用阳之脏。肝阴不足,肝失柔润,诸筋失于濡养则可见于抽搐、抖动、震颤、痉挛等;肝失条达,肝郁阳亢则有头晕目眩,甚则气血逆乱而昏仆等症。病机已明示于医家,病及内脏,而责之于肝,故指导临床从肝论治则不言而喻。然治肝之法,有疏肝、柔肝、养肝、平肝、清肝等诸法,必当辨其病因之由而施法处方。
【验案1】头痛风动,柔肝论治
唐某,女,65岁。2003年12月10日初诊。
主诉:头持续性作胀、掣痛8年。
患者自诉,自1995年起,睡眠渐差,整日重胀头晕不爽,终致头痛不休,且伴脑中噼啪作响,耳边似有风声呼呼,日夜纠缠,或有程度轻重之时,甚是痛苦。在上海某市级医院做颅脑CT及脑电图检查,均无异常提示,脑血流测定为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患者多方求治中、西医,鲜效。时诊:头痛抽掣昏胀,血压正常。双眼沉重有压迫感而难睁开,双目干涩充血。头痛剧时可有不自主头摇动。夜失眠,心烦易怒,口干入夜尤甚,皮肤干燥,常有皮疹起伏瘙痒,二便尚调。舌质暗红,苔薄淡黄少津。初观此头痛为肝阳亢盛之属,然细辨患者头痛剧时有头动摇,脑中风响,皮疹起伏,此乃风之征象,双目干涩,口干夜甚又为肝阴虚之见。故辨其证属肝阴不足,水不涵木,阳亢风动。治拟滋水涵木,清平肝风,佐以解郁活血。拟方:女贞子、桑椹子、生地、龟板各15g,龙胆草6g,生山栀10g,夏枯草20g,珍珠母、石决明各30g,天麻12g,钩藤15g,赤芍、丹皮、郁金、红花、桃仁各10g,丹参15g,炒地龙30g,全蝎3g,炒酸枣仁30g。7剂。
药后头痛目胀霍减,病人形容为“头部揭去一层壳,眼部搬去两块铅”,夜能入寐但易醒。再诊见双目仍充血,急躁易怒,且有潮热阵作。舌质暗红,苔薄,脉滑。初已见效,守法继进。上方去女贞子、桑椹子,加青龙齿30g,百合15g,知母10g。续服7剂。
三诊来诉:头痛程度大减,且仅局限于颠顶,双目充血基本消退,睁开正常,口干稍觉,皮疹复现,瘙痒脱屑。上方去龙胆草、红花,加紫草20g,凌霄花15g,白鲜皮15g。14剂。
此后守法略事加减,服药共两月余,头痛基本消失。劳累用脑过度偶有发作,但能自缓。
按语:此证历经8年,虽无明显器质病变,但患者却倍感痛苦。观前医之法,有清肝泻火龙胆汤之意,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之用,亦有重镇潜阳平肝之图,均不失为治疗头痛之常法。笔者踏前人之路,幸有捷径,弃单一之法,取诸法之融,增其滋水柔肝之用,且为君药之主,竟获良效,实切中其肝为体阴用阳之器,肝之舒缓条达,全赖阴血之濡养,体失所养,用之阳亢,阳亢风动则诸症叠起。单施清肝平肝,强制难平,更耗其阴,而滋水涵木以柔肝体,育阴而息内风则平肝清肝之效托显,头痛自解。
二、诸寒收引,皆属于肾
寒主收引,指寒邪具有收缩、牵引、内敛之特性,具体症状可表现出腠理的闭塞,经络筋脉的收缩、拘挛,气血的凝滞,而见有肢体关节疼痛、脘腹急痛,即《素问·举痛论》言“寒则气收”。在五脏病机中,认为内寒所生多由肾阳之衰所致。肾为先天之本,内藏元阴元阳,能温煦激发全身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之阳,肾阳能促进机体之运动、兴奋和气化功能,所以肾阳旺则全身之阳气皆旺,肾阳虚则全身之阳皆衰,张景岳《类经图翼·大宝论》强调指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故肾阳不足,寒从内生,脏腑、经络、筋脉、形体、诸窍、诸骸均失温养而见功能低下,气血运行迟缓,筋脉痉挛拘急、收引、疼痛,伴有畏寒肢冷,面色苍白,精神萎靡等。当然阴寒所胜,应辨内外之由,外邪入侵,客于经络关节也可见拘挛疼痛,如侵于关节则疼痛屈伸不利,客于太阳之经络可见项背僵硬不舒、头痛等症,但外寒多可引动内寒,影响到肾阳,故《内经》五脏病机中强调诸寒之症状表现均应重视温肾之阳。
【验案2】寒滞痛经,温肾论治
周某,女,26岁,未婚。2003年7月2日初诊。
主诉:原发痛经10年。
患者15岁初潮不久始现痛经,且背部常发皮疹痤疮起伏。近年来月经周期推迟,痛经渐重,每至经行第1天小腹开始隐痛,并渐加剧,伴头痛泛呕,面色苍白,冷汗,需服止痛片方可缓解,造成患者很大的心理负担。曾服中药1年,初服药痛经减轻,但两个月经周期后,腹痛更甚,又添头痛,故放弃治疗。刻诊:末次月经2003年6月29日,前次5月10日,现未净,经行第1天因未提前服止痛片,而小腹坠痛如绞,伴头痛,呕吐1次,后服止痛片得渐缓。平素小腹及腰骶部畏寒喜暖,却常感口干喜热饮,带下量多质稀,近数月来,月经周期迟后15~25天。B超检查:子宫及附件未提示异常,背部见有散发性皮疹。舌尖红,苔薄白,脉细涩。方拟《金匮要略》温经汤加减:吴茱萸3g,艾叶3g,桂枝6g,当归12g,川芎6g,生姜5g,制牛膝9g,乌药9g,白芍12g,香附9g,川连3g,菟丝子15g,肉苁蓉15g,杜仲15g,红花9g,炙甘草6g,肉桂3g。经行前于上方中加细辛、全蝎以增强温通化瘀止痛之力,而细辛、吴茱萸又可上颠顶通脑络而治头痛。
此法调治后第1个月经周期痛经明显有减,头痛、呕吐未作,月经周期迟后6天,背部皮疹隐而偶发,原方略事出入调治3个月经周期,痛经基本已平,仅在经行时稍有少腹坠胀。月经周期落后仅2~3天。嘱经后服乌鸡白凤丸滋补温养精血,经前服用艾附暖宫丸,以温肾暖宫,成药缓图善后以固疗效。
按语:该女有腰骶少腹畏寒喜暖,带稀而量多,为虚寒内盛可见。“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肾中命火,系人身阳气之根本。肾阳虚,冲任、胞宫失于温煦,每于经行,血海空虚,内寒更盛,则胞络收引拘急则痛经作。阳虚血寒,久不得温解,则血行滞缓,寒瘀交结,痛经更甚且经水周期延迟。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若寒凝血瘀阻于脑络则头痛。肾阳不能温煦脾胃,中焦寒盛,胃气失于和降,则可呕吐。肾阳虚不能蒸化水液而上承于口,故患者常有口干之现,然毕竟虚寒之本,虽有口干但思热饮。心火上炎不能下温肾水则见舌尖红,此证应属虚寒痛经。遵“诸寒收引,皆属于肾”之教,以温肾暖宫、散寒通脉为治则。方中肉桂、吴茱萸、艾叶,温经散寒通脉;乌药、香附,温散阴寒,行气止痛;白芍、甘草缓急止痛。前均以温散已凝之寒,通缓已滞之脉为首要。菟丝子、肉苁蓉,温补肾阳,培补命门为治本;当归、川芎、红花,养血活血调经以温行血运,化其血瘀;半夏和胃降逆,共以为佐。川连、肉桂,清心火,引浮阳下归真元以为使。
三、诸气 郁,皆属于肺
郁,皆属于肺
肺为五脏之华盖,主一身之气,司呼吸而喜宣降。是五脏中与气关系最密切之脏,肺对全身的气机起着调节的作用,肺之宣降呼吸即是气机的升降出入在肺中的具体表现。而肺气的升降出入又带动着全身的气机进行着升降出入的运动。肺的肃降正常,则呼吸匀调,呼浊吸清,气之生成与气机调畅也就能保持正常。肺的宣发正常,则能宣散卫气于全身,发挥固表御邪,温养脏腑、肌肉、皮毛,调控腠理开阖等作用。而一旦肺气失宣,则会出现卫气闭郁,易受外感,恶寒无汗,或汗湿不得宣透而肌肤疹痤郁疖。若肺气失降,水道失通,则痰湿壅滞,气促胸满等。故《内经》提纲挈领,高度总结,凡见有气机 郁,胸满壅滞者,从肺论治,宣肺、降肺、肃肺、开宣
郁,胸满壅滞者,从肺论治,宣肺、降肺、肃肺、开宣 郁以畅通气机,顺气之升降而为之。
郁以畅通气机,顺气之升降而为之。
【验案3】胸闷喘息,通腑肃肺
邱某,男,37岁。2003年11月30日初诊。
主诉:胸闷,喘促1周。
近1周来,患者自觉胸中弊闷重压感,呼吸不畅,喘促息满,口干思饮,饮不解渴,偶有咳嗽,咯痰不畅,大便素干结难解,常数日一行。病人自称身体向壮无疾,望舌质微红,苔黄浊少津,脉沉滑。就诊时段,病人饮水不断,且息粗气促,因正值秋燥之时,病人口干,咳而少痰,便干结,辨证属肺燥失降,治以润燥宣肺清肃,方用清燥救肺汤加减:玄参15g,麦冬15g,生地15g,麻仁15g,枇杷叶12g,鲜芦根30g,冬桑叶12g,生甘草6g,冬瓜子2g。7剂。然时过3天,患者再临,诉上药服后,喘闷未解,大便两天1次,虽有所见软,但黏滞难行,反排出量少,更增腹胀之苦,故余剂未尽再诊。展前方,心思量,莫非是前面辨证有误?然谬在何处?细斟酌其主诉,胸闷憋喘气促为主,而非咳喘。经云“诸气 郁,皆属于肺”,所涉之脏在于肺无疑,但肺气不降而壅满胸中,病机何在?忽思病人大便素干结,数日乃行,肺与大肠相表里,腑气不通,肺气不降,若肠腑一通,岂不是肺气得通降,胸满得宽而气促喘息可平?前之着眼于燥,而疏忽于气,润而不通怎收良效?复立通腑泻肺之法,方以泻白承气汤加减,3剂便通气降而喘促平。
郁,皆属于肺”,所涉之脏在于肺无疑,但肺气不降而壅满胸中,病机何在?忽思病人大便素干结,数日乃行,肺与大肠相表里,腑气不通,肺气不降,若肠腑一通,岂不是肺气得通降,胸满得宽而气促喘息可平?前之着眼于燥,而疏忽于气,润而不通怎收良效?复立通腑泻肺之法,方以泻白承气汤加减,3剂便通气降而喘促平。
按语:肺主一身之气,为华盖之脏,肺气的宣发、肃降直接影响着全身气机的升降调畅,尤其上焦气壅 郁,更是与肺气不得宣降直接相关,然肺虽为主气之脏,但令肺气失于宣降之因并非仅肺一脏,诚如《素问·咳论》所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诸气
郁,更是与肺气不得宣降直接相关,然肺虽为主气之脏,但令肺气失于宣降之因并非仅肺一脏,诚如《素问·咳论》所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诸气 郁,从肺表现,但治病求本,尚需寻根究因。本案一诊失治,未重气逆而轻从燥论;二诊中,从气满息促仍肺气壅滞失肃之外在表象,推其腑气不通,阻其肺气肃降为其病本,表里相系,通腑仍为泻降肺之壅滞之气,不失经文训导之意。
郁,从肺表现,但治病求本,尚需寻根究因。本案一诊失治,未重气逆而轻从燥论;二诊中,从气满息促仍肺气壅滞失肃之外在表象,推其腑气不通,阻其肺气肃降为其病本,表里相系,通腑仍为泻降肺之壅滞之气,不失经文训导之意。
四、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脾主运化升清,统摄血液。脾之运化,包括运化水谷与水液。饮食入胃,在脾气的运化下,腐熟吸收,化生精微,转输周身,营养脏腑经络、四肢百骸、表里内外,故《素问·厥论》有言“脾之为胃行其津液者也”。《素问·奇病论》有言:“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而脾主运化水湿功能体现在水液代谢中的有调节、推动、运转作用。将人体所需之水液吸收转化,布散全身而发挥滋养濡润作用,同时也将利用后的多余水液,及时转输于肺和肾脏,通过肺之宣降、通调水道和肾之气化,转化为汗液、尿液而排出体外。因此,一旦脾之运化失健,水液代谢失调,不能正常利用和排出,则停滞潴留在体内,产生水湿痰饮、肿满等病理变化,临床常见脾虚生湿水肿,及水湿痰饮滞留在肌肤、经络、肠胃等处,因痰湿而肿满的病机变化与脾脏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故治疗上要考虑脾的功能特性来论治。
【验案4】痰湿闭经,从脾论治
益某,女,27岁。2001年7月28日初诊。
患者自1998年始间断性停经,每遇停经3个月不行则自服安宫黄体酮促经,形体渐胖。B超示:子宫:35mm×34mm×21mm,右侧卵巢(ROV):16mm×14mm×13mm,左侧卵巢(LOV):16mm×15mm×12mm。激素测定:黄体生成素(LH):20.4mIU/mL,促卵泡成熟素(FSH):9.6mIU/mL,比值>2。时诊:末次月经2001年4月中旬,因已有3个月经水未行,故来诊前1天已自服安宫黄体酮。病人平素胸闷气短,咽中痰黏,四肢欠温,体胖(身高160cm,体重73kg),带下质稀,近1年来量渐少,大便干稀不调。舌质暗紫,苔薄白,脉细。证属痰湿阻滞,壅塞冲任胞络。因其已服黄体酮,故先行疏通气血,顺势利导为之,并嘱测基础体温。
二诊(2001年8月25日):8月5日经行,量少,6天净,基础体温至今36.3~36.4℃,平台走势未上升。自诉除前症外,而有口淡乏味,口干不思饮。舌脉同前。治拟运脾化湿,理气行滞,活血调经。方用六君四物汤加减:白术12g,苍术12g,陈皮12g,半夏12g,茯苓15g,香附15g,当归15g,川芎6g,砂仁6g,炒山药15g,炒谷芽、炒麦芽各15g,川朴9g,石菖蒲12g,肉苁蓉15g,仙茅15g,淫羊藿15g,炒补骨脂15g。14剂。嘱观察基础体温变化。
三诊(2001年9月8日):经期已过而经水未按时而至,基础体温于9月2日上升至36.5~36.7℃,现已持续5天,咽中痰黏已消,仍感胸闷不舒,大便已实,日行1次,法已奏效,于上方加全瓜蒌15g,红花10g,桂枝6g,川牛膝10g,益母草30g。再继7剂。
四诊(2001年9月15日):患者欣告,9月12日经行量正常,有块,稍有腹痛。
后守上法于前方随兼症出入,每于基础体温上升10天左右加活血行气之品,当血海盈满之时则行推动之力,顺势而促其溢泄。后分别于2001年10月28日、12月7日及2002年1月10日、2月21日,每月不服用黄体酮而经水能自行,周期稍有迟后,患者坚持服药近1年。自2002年6月始间歇服中药,周期维持在30~40天,体重也渐下降,由原73kg减至65kg。2003年1月电话随访,月经已正常而行。
按语:“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痰湿内盛,责之脾失健运,痰湿困阻,阳气不运水湿,不能蒸化上承,故胸闷,痰黏,四肢不温,口干不思饮;水液不能布运,而湿聚痰盛,阻滞气血,壅塞冲任则经闭不行。此例病在冲任,因在脾虚,病机在痰湿,故从健脾入手,健脾气,振脾阳,化痰湿,并培肾元而温脾土,气化水湿而驱痰阻,并疏理阻滞之胞络,使气血生化正常,冲任充盈,地道通畅而经水按时而至。
五、诸痛痒疮,皆属于心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语出《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帝曰:愿闻病机何如,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意为各种疼痛、作痒及疮疡的病患都与心有关。
中医认为,心主血脉,五行属火,若心火亢盛,营血有热,热壅气血,脉络阻滞则作疼痛;若营血怫热,血脉壅滞,郁结皮腠,无以透达则作痒。若心火灼热,血脉壅滞,瘀结肌肉,日久血壅肉腐则发疮疡,故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进一步明确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
诸痛痒疮多属皮肤科或外科的疾患,笔者涉猎皮肤病的治疗,是以收治1位日光疹病人起始。良好疗效,使笔者对“诸痛痒疮,皆属于心”顿悟。早期室女陈某,因月经不调而来就诊,调治3月病情向愈,月经周期已趋正常。而时值入夏,故劝其可停药观察,可此女出言:“每至夏季,皮肤常出皮疹瘙痒,今夏又起,西医诊断为日光疹。多用激素类软膏外涂,但总是起伏不彻,我信任您的医术,是否给我予以治疗?”因笔者并不擅长皮肤病专科,确有恐药之无效之忧,但当时患者求医,岂有推却之理,于是详问病情,细辨症状,望其皮疹粟状尖红,布散稠密,抚之碍手,望其舌象,舌尖红少苔。四诊所得,属心经有热,累及营血。汗为心液,交结皮腠,不得透发,郁而为疹。《内经》有“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之训,遂以清心凉血、甘凉透表为法。药用川连、莲子心、竹叶、六一散清心利尿,热从下出;牛蒡子、蝉蜕、薄荷轻宣透发于外;生地、紫草、丹皮、赤芍、白鲜皮等清营凉血消疹。1周疹隐脱皮屑,自后曾随访得知未再复发。
心属火,其气通于夏,夏暑炎热,同气相加,故夏季多见口疮舌糜,皮腠疮疖,汗疹痱子。并多心烦失眠、小便短赤等火热之症。而通过清心凉血、消暑导赤等治法,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