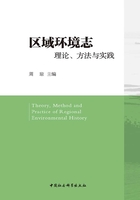
四 口述史料中的技术与环境
环境史研究首先应该关注人是如何生存的?本质上,人如何生存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史的问题。环境史研究为何要强调技术的作用?技术史研究技术自身演变过程,但技术本身的形成与演化离不开外在环境。一般而言,人是在理性引导下、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故而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20]实践反馈回的环境信息也直接影响着区域人群的环境认知。
首先,技术(Technology)依赖于环境存在,也是环境得以维系、平衡或失衡的重要因素。环境是技术产生的基础,影响技术的形成与演变。对于鱼坝结构,咸丰《邓川州志》中就有过简单的记载:“(渔沟)沟中就埂脚织竹,如立栅,曰鱼坝。栅斜开向上,就对岸为口,曰坝口。凡鱼性逆水行,河水由沟如海,海鱼衔尾入沟。触栅,栅水喷沫,鱼愈跳泼,循栅进,既入口,渔者以网作兜盛之,白挺跳泼如梭织,尽昼夜所获,莫可思议。”[21]这种在渔沟中设竹栅的捕鱼方式到民国陆鼎恒考察时依旧如此,陆对鱼坝的记载也更为细致,其言:“二十八年(1939)十一月,我在大理一带考察洱海附近的生物状况,就听见大理县建设局长张勉之君对我谈到下江尾的捕工鱼业。他说鱼坝上支板架茅为屋,以供渔人居处,屋旁就是鱼窝,随时以网捕捞取之。所以渔人可以长袍马褂,衣履不湿,一夜千余斤,真算是奇观了。及至一月十八日我离开邓川时,承该县建设局长杨应侯君亲伴送至下江尾来看工鱼坝,方得细视他的构造。”这种早年的调查文献,本质上也是口述史料,“每一鱼沟只能建鱼坝一个,因为他(它)把整个的河身截断,几乎没有一条鱼可以穿过,所以不能建第二个坝。每个坝全用竹子编成立栅,其密度足以阻止工鱼的通过,然后树栅于沟中,先在下流横截全沟之半,然后在沟的中央纵行而上,分沟为左右二部,此段长约二三丈。最后在向着上流的一端,用竹栅横行封闭,恰好亦当沟宽之半。在纵行栅之近上流端处,另以小栅二栽成八字形口,尖顶正对坝底,即是向着上流的一端。竹栅用粗木横固定于岸上,即借着横木为下架,在上面建一个茅屋,以为渔人食卧之所;茅屋门向着上游,门前用木板搭一平台,其下正当着坝的上流末端,亦即是鱼窝之所在。”[22]这种立竹栅于渔沟中,并在渔沟之上搭建茅屋以方便捕鱼的鱼坝设施,尽管陆鼎恒的描述已经十分清楚,但笔者仍无法完全构想出鱼坝的真实面貌。所幸的是,笔者在当地水利文献中发现了一张60年代的“鱼坝”照片,与陆鼎恒描述的情况完全一致,鱼坝的立体感才随之形成。
其次,当环境发生改变后,依赖于环境而存在的技术(包括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也将发生变革。因此,在环境演变过程中消失了的技术就需要回到田野中去找回,与亲身经历者进行口述访谈无疑就是最有效而直接的手段。
传统时期的鱼坝技术在当地维持到什么时候,为何消失?据当地人回忆,鱼坝捕鱼技术在80年代以后逐渐消失,渔沟也在90年代后被农地侵占:“鱼坝一般扎在河道的入海口处,设一道鱼坝。在鱼坝上面可以搭一个窝铺睡觉。以前渔沟入洱海处的宽度大致在6—7米,鱼坝用细的毛竹编成,宽度与河道相同。细毛竹一则好用,二则由于质地坚硬,比较耐腐烂。鱼坝做好后,一次可以用2—3年。鱼坝高度在2米左右,用草绳编成网格状,有一定的缝隙,可以漏水。在鱼坝上游还有一道小的拦水坝,一般是土坝,土坝有放水设施,打开一个缺口,可以人为控制。要捕鱼的时候就将土坝堵住,当土坝与鱼坝之间的水位下降,即可捕鱼。土坝与鱼坝之间长30—40米,渔沟宽6—7米。鱼坝在80年代还有,90年代基本就没有了。20世纪70年代末弓鱼逐渐灭绝后,鱼坝里的鱼还有一点鲫鱼、鲤鱼、草鱼。90年代以后渔沟里就基本没有捕鱼的了,一则这种捕鱼方式落后,当时在洱海里发展了网箱养鱼;二则渔沟里的鱼逐渐变少了以后,弥苴河中上游的整体调蓄水能力不断提升,以前依靠渔沟泄洪水的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改变。于是,渔沟在本地农户的不断侵占下越变越窄。”[23]鱼坝、渔沟、弓鱼三者形成完整生态链条,其中一个环节出现断裂,整个生态链也将不复存在。随着弓鱼的减少,渔沟与鱼坝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鱼坝”从技术层面上看并不复杂,但却在当地维持了数百年。可见,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发展并不一定要追求技术的革新速度,而是要努力让技术与所依赖的环境形成良性共生。从当地鱼坝捕鱼技术的发展演变看,技术简单正反映了当地弓鱼生境的稳定与和谐。据访谈者陈述,在弓鱼多的时候,渔户坐在船上顺手就可以捞起鱼来。这种说法是否真实虽未及查证,但也能大致反映当时本地鱼类资源之丰富。这种鱼类资源与简单技术之间维持了数百年的平衡,但却在近几十年被彻底打破。
对于弓鱼的消失与灭绝,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云南鱼类志》解释为:“近年来由于洱海引入外来种与大理裂腹鱼之间的竞争激烈,同时由于山溪小河筑堰引水,大部分产卵场遭到破坏,致使大理裂腹鱼数量大减,现已极少见,成为濒危种。大理裂腹鱼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若能控制外来种,改善环境,同时积极进行驯养,则不但可保住珍稀物种,而且可望逐渐恢复它的数量。”[24]指出导致弓鱼濒危的原因有二:其一,洱海外来物种的引入;其二,山溪中筑堰引水。而对于下游西洱河电站设置并未提及。而在当地的走访中,多数人提到弓鱼消失与在洱海出水河(西洱河)上建电站有关。而这中间的关联度是怎样的,应该需要有科学的数据支持与相关指数分析,对此问题笔者会在以后的文章中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历史研究不应该僭越学科边界去替自然科学找寻“真理”。当然,作为从事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学者,应该要有这种探知真理的信念,但不可轻易对科学问题给出结论。对于技术与环境关系的解释分析,要警惕口述访谈中被访谈者的“科学”归纳,而应该更多关注访谈对象对历史事实的细节陈述,并多方考证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