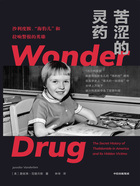
第2章
药物的制作和使用基本分为两个时代——自然药物时代和实验室药物时代。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第一个时代。那时,“药”指的是用臼和杵将草药、果实、藤蔓和菌类捣碎后混合而成的东西。尼安德特人用杨树皮来缓解牙齿脓肿。能产生抗生素的霉菌就是他们的碱式水杨酸铋咀嚼片(Pepto Bismol)。大约公元前1850年的“卡洪纸草文稿”(Kahun Papyrus)是最古老的人类药物记录之一,详细记载了用奶、油、椰枣、药草和啤酒做的各种涂抹阴道的药膏和药水。大约300年后,108页的“埃伯斯纸草文稿”(Ebers Papyrus)描述了治疗四肢僵硬、眼疾、骨折、烧烫伤、寄生虫、坏疽病、水肿和肝病的药物。在数百种药物中,柳树皮(阿司匹林的前身)被用来止痛。萨满、巫医和男女郎中用这些药给人看病。最终,药房让这个行当变得正式起来,把药水装进瓶子,贴上标签。但这些药店出售的仍然是自己在后院熬制的药物。它们从事的不是化学,更像是“混合学”。
1832年,一名有远见的德国人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可称为现代制药之祖的李比希1803年出生在小城达姆施塔特。他父亲是合成油漆、清漆和颜料的化学品制造商。李比希先是在父亲的车间里帮忙,后来又去当地一家药房当学徒。作为正式教育,尤斯图斯在普鲁士波恩大学享誉欧洲的化学专业获得了化学学位,又在巴伐利亚的埃尔兰根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李比希最终成了吉森大学的教授,但他的科学远见超过了学术成就。他总是在思考如何为化学品找到新用途,他也喜欢在实验室里鼓捣各种各样过去未曾研究过的材料。李比希发现氮和微量矿物质是植物的关键营养素。这一发现促成了化肥产业的快速兴起。他做出牛肉精后,成立了李比希肉制品公司(Liebig’s Extract of Meat Company)。他从海藻和真菌中分离出了液体氯仿(就是劫持者手中的白布浸的那种药水),这种通用麻醉剂是19世纪医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不过李比希最大的成就是制造出了水合氯醛。1832年,他把乙醇(粮食酒精)倒入盛着硫酸的烧瓶,然后把气味刺鼻的绿色氯气通入瓶里的混合液体中。这不知怎么造成了氯和乙醇分子中原子的互换,产生了白色的晶体。李比希起初称其为“chloral”(氯醛)——这是把“氯”(chlorine)的前几个字母“chlor”和“酒精”(alcohol)中的“al”合到一起造出的一个单词。乙醇和氯本身都没有医药用途,但李比希新制成的白色结晶C2H3Cl3O2后来被发现有镇静神经系统的作用。与以前的药物相比,他制造出的这种新分子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作为人在实验室中造出的产物,水合氯醛成为世界上第一种人工合成药。[1]
不出30年,水合氯醛(可以吞食的药粉,不用注射)取代了吗啡,成为精神病院和富裕人家的首选镇静剂。因为创造发明出的分子可以申请专利,所以发明者坐收厚利。两个已有的产业赶忙抓住了这个利润丰厚的新机遇。
药房早就在兜售加了鸦片的糖浆,还给这类糖浆取了“霍珀止痛剂,婴儿的好朋友”这样的名字。现在它们纷纷转向合成药。李比希家乡的一家药房默克(Merck)在189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制药公司,[2]瑞士的霍夫曼罗氏公司(Hof mann-La Roche)、英国的宝来惠康公司(Burroughs Wellcome)、法国的普朗兄弟公司(Poulenc Frères)和美国费城的史克公司(Smith, Kline&French)[3]紧随其后。
欧洲纺织业主也抓住了这个机会。纺织公司已经在从煤焦油中提取化学物来生产合成染料,所以有现成的研究和制造框架。李比希成功研制出水合氯醛后,各纺织公司开始仔细研究染料合成过程中那些黏糊糊的副产品,看哪些原子有可能被用作下一种灵药。
这就是拜耳公司(Bayer)的故事。1887年,这家德国染料公司发明了退烧镇痛药非那西丁(Phenacetin),10年后又发明了适于治疗各种疼痛和发烧的乙酰水杨酸。这种被定名为“阿司匹林”的药成了世界上第一种超级畅销药。[4]接下来,拜耳公司推出了用巴比妥酸制成的一类新药:巴比妥酸盐。这类药不只缓解身体上的疼痛,还能减轻精神痛苦。1903年,佛罗那(Veronal,巴比妥)问世,9年后又推出了更强效的鲁米那(Luminal,苯巴比妥)。巴比妥酸盐作为助眠药、麻醉剂和抗惊厥药大受欢迎,作为日常改善情绪的药物更是风头一时无两。
很快,阿片类药物这种吗啡和可待因的廉价合成品也上市了,有羟考酮(1917年)、氢可酮(1924年)、哌替啶(1939年),还有美沙酮(1939年)。随着改造分子的技术日臻完善,出现了专门的特效药。1939年,帕克—戴维斯公司(Parke-Davis)的地仑丁(Dilantin)成为第一种能够治疗癫痫的非巴比妥特效药。[5]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药物——无论是自然药物还是实验室药物——成为重要的军事资产。在太平洋战争中,配备了阿的平(Atabrine)和奎宁的部队能更有效地治疗受疟疾折磨的战士。为了准备诺曼底登陆,美国政府认购了私营部门生产的磺胺和青霉素,以备治疗伤员。改善情绪的合成药也在战斗中派上了用场。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在执行自杀任务之前会注射甲基苯丙胺。盟军士兵靠吃苯丙胺来解乏。野战医院给患弹震症[6]的士兵吃巴比妥酸盐。德国国防军的部队在对法国发动闪电战之前吃一种叫斯图卡药片(Stuka-Tablette)的甲基苯丙胺来鼓劲。希特勒自己对药物也很在行,“二战”期间一共注射了约800次针剂,包括经常注射羟考酮。[7]发现鲁米那这种较新的巴比妥酸盐大剂量使用有毒之后,希特勒首选用它来施行大规模安乐死。
战争加速了药品的生产。这意味着轴心国落败之际成了美国制药公司大展宏图之时。此外,盟军还派遣由军人和文职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队跟随开路的大军冲进德国的工厂、实验室和图书馆,没收各种军事、科学和工业记录。一次,两名盟军士兵在山中发现了一个混凝土掩体,上面标着“Achtung! Minen!”(小心!地雷!)的字样。两人通过抛硬币来决定谁上,输了的那人把吉普车开到掩体门口,屏住呼吸,踩下油门。没有地雷爆炸。门被撞开了,现出一个1 600英尺深的竖井,竖井底部的一筒筒液氧下藏着德国的全部专利记录。[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迫使德国交出知识资产,比如拜耳公司在美国为“阿司匹林”做的商标注册(所以杜安里德和CVS这两家连锁药店可以出售它们自己的“阿司匹林”)。1917年的《禁止与敌国贸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甚至允许美国政府没收德国的化学专利,然后廉价发放给美国公司。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劫掠并没有条约或国会法案的准许,也没有经过公共讨论。
战后最大的天降横财来自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它是由6家德国公司组成的财团,包括拜耳这个几十年来全世界化学和制药工业的老大。从法本获得的资料应有尽有,包括制造固体燃料、合成橡胶、纺织品、化学品、塑料、药品和5万多种染料的工艺方法。制药记录尤为宝贵。作为现代制药业的新月沃地[9],德国化学工业的产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远超所有其他国家。据估计,战后被剥夺的德国知识产权总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10]1945年8月25日,哈里·S.杜鲁门总统悄悄颁布法令,将德国的100万份专利文件划归美国公司所有。德国因被迫做出这些战争赔偿而愤怒哀叹,但美国人对德国最大的法本公司不抱同情,特别是在该公司战时的劣迹被揭露出来之后。
1947年5月3日,美国对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24名管理人提出战争罪指控。[11]法本公司不仅是希特勒竞选活动的最大金主,[12]而且建造了奥斯维辛—莫诺维茨化工厂,至少3万名囚犯在里面死于非命。[13]法本还拥有德格施公司(Degesch)相当多的股份,而令100多万囚犯命丧黄泉的臭名昭著的齐克隆B(Zyklon B)毒气就是德格施生产的。[14]
“美国诉卡尔·克劳施等人案”(U.S.A.v. Carl Krauch et al)是13场著名的纽伦堡审判中的第6场。被告人中有法本公司的高级研究员奥托·安布罗斯(Otto Ambros)博士。魅力十足、衣冠楚楚的安布罗斯是希特勒的顾问和首席化学武器工程师。[纳粹研发的神经毒气“沙林”(sarin)中的“a”代表的就是“安布罗斯”。]除了帮助建立奥斯维辛—莫诺维茨化工厂外,他还在迪赫恩福尔特建了一个强迫劳动营来生产神经毒气。据称他曾在奥斯维辛安排用拜耳公司生产的化学品和毒药在囚犯身上做实验。集中营给拜耳公司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人体测试受试者。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与拜耳公司总部的通信显示,拜耳曾要求集中营提供妇女来测试一种“新的催眠药”[15]:
请为我们准备150名尽可能健康的妇女。
150名妇女的订单已收到。尽管她们身体消瘦,但状况还是令人满意的。我们会及时把实验情况告知你们。[16]
那150名妇女无一幸存。[17]
另外200名得了脓毒性咽喉炎的女子被在肺部注射了一种拜耳生产的抗菌药物。[18]所有被注射的人都在万分痛苦中慢慢死去。一名曾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乌克兰女孩后来回忆说,在3年的时间里,一个纳粹医生经常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床上,强行让她吞下各种标有“拜耳”字样的药瓶中的药片。战争结束后,她发现自己丧失了生育能力。[19]
安布罗斯和其他受审的法本主管声称,他们不过是中层管理人员,只管处理文件,不知道集中营发生的事情。“我只是个化学家。”安布罗斯抗议说。[20]虽然被任命为造成数万人丧生的项目的主管,但安布罗斯说自己的头衔不过是“荣誉性的”。然而,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认为这些白领医学主谋构成了独特的威胁,也犯有独特的罪孽。泰勒说:“主要的战犯是这些法本公司的罪犯,不是那些狂热的纳粹疯子。”[21]毕竟,是法本公司为纳粹提供了齐克隆B毒气和鲁米那这些不流血就能置几百万人于死地的手段。在专业的光鲜外衣的保护下,这些主管从遥远处即杀人如麻。若是让他们重获自由重操旧业,会发生什么?
泰勒的团队担忧,“如果不把这些罪犯的罪行公之于众,如果让他们逍遥法外,那么即便希特勒还活着,他对世界未来和平构成的威胁也远远不如这些人”。[22]
1948年7月30日,13名被告因“无视基本人权”被判处徒刑,安布罗斯的刑期最长,为8年。[23]到1951年,法本公司在法庭判决的打击下土崩瓦解。盟国将专利据为己有抽空了其他德国药业巨头的力量,新入场的公司意外地突然获得了施展空间。
有一家名叫“达利—韦尔克、莫伊雷尔和维尔茨”(Dalli-Werke,Mäurer&Wirtz)的小型制皂公司,老板是两兄弟,都是狂热的纳粹支持者。[24]他们成立了一个制药分公司来吸纳和利用近来大批失业的纳粹研究人员。这家分公司被命名为“格吕恩泰化学公司”,最终聘用了奥托·安布罗斯担任公司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古色古香的施托尔贝格镇坐落在德国临近比利时边界的丘陵地带。它曾经是黄铜生产重镇,但是到19世纪中期,镇里的制造商已经把业务扩展到了玻璃制造、纺织和男子服饰等多个领域。
1845年,米夏埃尔·莫伊雷尔(Michael Mäurer)和继子安德烈亚斯·奥古斯特·维尔茨(Andreas August Wirtz)在施托尔贝格建起了一座用动物油脂做肥皂的工厂。他们的产品很快出现在德国各地和邻国的商店里。到世纪交替之时,“莫伊雷尔和维尔茨”这个名声好、利润高的公司开始为自己的产品注册商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家公司大发横财。公司的管理权当时已经传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孙子赫尔曼和阿尔弗雷德·维尔茨手中。维尔茨兄弟是纳粹党员。据说,在推动一项雅利安化方案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强夺两家犹太人拥有的公司——柏林的德林·韦尔克公司(Doering Werke)和维也纳的里瓦公司(Riva)——扩大了业务。他们还得到了几百名奴工。[25]
然而,战争即将结束时,纳粹的补贴没有了,国家被占领,城市被夷平,食品稀缺。两兄弟只得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根据公司的传说,在大战尾声的一次空袭中,肥皂厂的经理、一个名叫雅各布·肖弗里斯特(Jakob Chauvristé)的比利时人和一名药剂师一起在防空洞里避难。那名药剂师预言,战争结束后抗生素会供不应求,而抗生素不仅生产成本低,而且利润很高。于是,1946年,阿尔弗雷德和赫尔曼把施托尔贝格一个废弃的18世纪炼铜厂改造成了他们新成立的制药公司的总部。这座三层石头建筑的墙上爬满了叶片闪亮的常春藤,屋顶是洋葱形的拱顶。推开白色窗框的窗子,下面的院子里满是盛开的杜鹃花。因为这童话般的景色,两兄弟给公司取名为格吕恩泰,意思是“绿谷”。
1946年12月23日,肖弗里斯特和赫尔曼·维尔茨正式登记为公司的董事。因为公司管理层的所有人都对药理学或医学一窍不通,所以他们赶紧雇了一位首席科学官:32岁的海因里希·米克特。米克特的药理学学位只读了一半,但他因在“二战”中作为德国国防军军医开展斑疹伤寒的研究而知名。为了研究疫苗,他安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给囚犯注射斑疹伤寒病毒,造成数百人死亡。[26]战后,为了躲避波兰当局的追捕,他逃到德国进入波恩大学读书,在那里应聘入职格吕恩泰。以傲慢自大出名的米克特后来成为沙利度胺事件里最大的恶棍。[27]
新成立的格吕恩泰公司也给许多其他前党卫军军官提供了职业庇护。公司的病理部主任是鼓吹“种族卫生”、帮助制定纳粹人口控制政策的马丁·施特姆勒(Martin Staemmler)。前党卫军营养检查官恩斯特—金特·申克(Ernst-Günther Schenck)医生也加入了公司,这对他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因为他开展的“蛋白质香肠”实验造成了数百名囚徒死亡,为此他被禁止在德国行医。1956年,公司还雇用了曾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首席医学官的海因茨·鲍姆克特(Heinz Baumkötter)。鲍姆克特虽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但提前获释。西德法院之后又判他犯了大规模谋杀罪,但因为他在苏联已经服过刑,因此就不必再在西德坐牢。就这样,两次被判犯有谋杀罪的鲍姆克特得以走遍德国,推销格吕恩泰的产品。
格吕恩泰搜罗党卫军人员的最大手笔是雇用了奥托·安布罗斯。安布罗斯被纽伦堡法庭判罪后入狱服刑,后提早获释,最终在格吕恩泰化学公司的董事会得到了一个肥缺。
格吕恩泰初次试水制药选择了抗生素。官方的公司史把这一决定描述成人道之举。据说公司看到亚琛边境地区被“切断了一切药品供应”,[28]想出力帮助。最初制造的产品是拿着美国的许可证生产的美国抗生素。这意味着要向美国专利方支付版税,己方的利润自然有限。只有发明药才能赚大钱,但来自大学和国际制药公司的竞争十分激烈,而给米克特做助手的药剂师威廉·孔茨(Wilhelm Kunz)经验甚至还不如米克特。
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很快发明出了两种新的抗生素:黄青霉素和短杆菌素。这些发现完全是偶然之得,几乎意外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几年后发现,米克特没有为这两种抗生素申请专利,于是有人指控说格吕恩泰其实是把德国战时发明中逃过盟国劫掠的漏网之鱼拿出来投入了市场。[29])
1948年,格吕恩泰已经在出售自己研制的抗生素,公司的投资猛增了6倍。[30]接下来,公司的生产线又增加了一种丹麦研发的名叫帕尔默500(Pulmo 500)的抗生素。这种药被用于治疗脑膜炎和肺炎,在德国卖得很好。但在1954年,德国的医生开始报告该药会引起病人的严重反应,它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比基本的青霉素高100倍以上。[31]开药的医生怀疑,格吕恩泰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也没有对这种药做过安全研究。他们说,这种药“在尚未发表充分的动物实验结果的情况下就被用在了人身上”。[32]3名西德科学家甚至指控格吕恩泰故意无视问题。但格吕恩泰仍继续出售此药,也未向医生发布警告。
然而在国际市场上,抗生素的竞争十分激烈。大型英美公司能多快好省地生产出各种抗生素。格吕恩泰的收入陷入了停滞。它急需一种新分子,以便向外国公司出售生产许可。
1954年春天,米克特指示研究人员开始研制一种治疗肥胖的利尿药。他让孔茨在碳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的基础上制造肽(像蛋白质一样的小分子[33]),并研究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对孔茨这个不熟练的药剂师来说,这样的指示太笼统了些,但现在有一名真正的药理学家指导他:波恩大学的赫伯特·凯勒(Herbert Keller)。凯勒的注意力很快集中到孔茨创造出的一种分子上,这种分子白色、无味,叫沙利度胺。这种物质没有显现出利尿的潜力,却在结构上非常近似正式名称为苯乙哌啶酮的巴比妥酸盐。[34]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催眠药和镇静药最初在精神病院被用来治疗精神错乱和神经紊乱,近来却广受普通民众的欢迎。似乎每个人都想借外力帮助自己放松和入眠。巴比妥酸盐类药物的需求猛涨,让制药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米克特和格吕恩泰签订的合同规定,他做出的任何发现只要赚了利润,都会分给他1%作为奖金。[35]于是米克特指示孔茨和凯勒专心研究这种白色粉末K17[36](意思是“孔茨发现的第17种副产品”)。(它的正式实验室名称phthalimodoglutarimide最终被缩短成比较容易念的thalidomide。)
在测试一种化合物的镇静催眠功效时,实验室开展的第一项实验通常是把这种化合物喂给大鼠,然后把吃了药的大鼠翻得肚皮朝上,看它能不能自己再翻过来。催眠药会扰乱动物的“翻正反射”(righting refl ex)。但没有记录表明格吕恩泰做过这样的测试。(有意思的是,沙利度胺并不影响翻正反射。)与此相反,格吕恩泰快进到了更加复杂的实验:把大鼠放到跑台上。正常的催眠药会减慢大鼠的速度,一般喂的剂量越大,速度越慢。沙利度胺没有通过这个测试。
许多研究者到这个程度就会放弃了。公司研制的新分子与巴比妥酸盐相似,却起不到巴比妥酸盐的作用,两者就像脾性完全不同的化学兄弟。另外,沙利度胺和已知的镇静剂不同,它的分子是不对称的,这意味着不同构型(confi guration)[37]的沙利度胺或许功效会有所不同。然而米克特仍然不肯放弃。这个分子药若是成了,公司就会一步登天。但若想把沙利度胺当作催眠药推向市场,米克特必须抛弃“睡眠的特点是协调能力丧失”这个前提。[38]他必须重新定义睡眠,并设计出一种前所未有,可以在实验室开展的实验。
“摇晃笼”做得相当复杂,笼子里有几根杠杆、一盆硫酸、几根铂丝和一个测量氢气释放量的装置。小鼠在笼子里晃动时,铂丝会浸入硫酸盆,使水电解,释放出氢气。格吕恩泰的研究人员发现,给小鼠喂了沙利度胺后,产生的氢气少了50%,这意味着老鼠晃动得少了。虽然小鼠并未进入睡眠,但公司把晃动减少解释为睡眠,因此把这种药称为催眠药。
格吕恩泰想把这种新物质算作催眠药有个很好的理由。各类巴比妥酸盐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过量服用会致死。然而,用沙利度胺开展的实验表明,无论吃多少都不会造成实验室小鼠的死亡。不会致命的催眠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超级畅销药。
从1954年5月到1955年5月,孔茨和凯勒一口气为沙利度胺和与之相关的物质申请了5项专利。他们提出的材料涵盖了每一种可能的生产工艺。在德国申请的专利列举了7种生产方法,后来在美国、英国、瑞士和法国提出的海外专利申请又增加了6种生产方法。然而,他们只顾忙着申请专利,却没有对使用这6种方法生产出的产品进行动物安全测试。在德国专利起初的5种生产工艺中,只有一种生产出了公司最终出售的药品,但公司并未用这种工艺生产出的药品来证明沙利度胺的安全性。事实上,格吕恩泰没有留下任何最初用沙利度胺开展动物安全测试的资料。10年后,德国当局要求看该药的实验数据时,格吕恩泰声称相关资料在公司的一次搬迁中遗失了。
后来,就连格吕恩泰对沙利度胺的“发现”也受到了仔细的审视。1955年春在美国和英国提交的专利申请很奇怪,它描述了该药对人的镇静作用,但那时还没有任何人体试验的记录:
这项发明的产品具有宝贵的治疗效能。它们能显著地降低机动性,即运动现象,且毒性很低。一般来说可以将它们用于“中心衰减”(植物性肌张力障碍)。这项发明的产品没有任何如马钱子那样造成外周性瘫痪的效果。
此外,这类化合物还有一定的解痉和抗组胺效能。这项发明的产品,特别是3-phthalimido-2,6-dioxopiperidine[即纯沙利度胺],大量使用时能有效助眠。[39]
1955年初,格吕恩泰仅刚刚完成几项在小鼠上的实验,它怎么可能详细阐明沙利度胺对人体产生的效果?临床数据从何而来?是不是在完成长期动物安全测试之前就给人吃了这种药?对于格吕恩泰,有些问题在后来几十年间一直如影随形:既然这种药没有对小鼠产生镇静作用,米克特的团队怎么知道它会对人起到镇静作用?公司里有人此前用过这种物质吗?鉴于格吕恩泰与党卫军医生的关系,沙利度胺是否在集中营里测试过?
格吕恩泰于1955年春开始正式人体试验,也提交了相关的资料。[40]公司把这种药发给9名德国医生,表面上是为了收集临床数据。结果并不理想。1955年12月16日,参加临床研究的医生,包括皮肤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神经科医生,在一次研讨会上向格吕恩泰报告了他们的试验结果。
4名医生喜欢这个药,但他们的试验方法粗糙草率。[41]赫尔曼·荣格(Herman Jung)医生在他的科隆诊所里只给20名病人用了沙利度胺,时间仅有4个星期。他还每月从格吕恩泰领取200德国马克作为随时需要他服务的预付金。面对立竿见影的效果,荣格似乎惊喜莫名:4名男青年克服了手淫的欲望;几个已婚男子也不再早泄,令他们的妻子十分欢喜。荣格宣称这种药“没有副作用”,[42]预言它一定能赚大钱。杜塞尔多夫的海因茨·埃塞尔(Heinz Esser)医生对350名病人展开了试验,他也对此药的镇静作用赞扬有加。但埃塞尔的试验只持续了12个星期,他后来注意到病人出现了头晕、发抖和耳鸣等副作用,就不再开这种药了。研讨会上还有另外两份对该药予以肯定的报告,但报告所依据的试验不是匆匆完成,就是记录得马虎潦草。一名医生给脑外伤的病人用了沙利度胺,说它的效果堪比脑叶切除术——似乎对这种药盛赞有加。
剩下的5名医生中,有4人拿不定主意。明斯特的卡尔·福伦德(Karl Vorlaender)医生注意到有些病人出现了恶心、眩晕和难以入眠的症状。另外,用药3个星期后还会上瘾。但当他要求格吕恩泰多给他一些时间以增加试验的时长和范围时,却遭到了拒绝。哥廷根的格哈德·克洛斯(Gerhard Kloos)医生不需要更多时间。他的3名同事自己试吃了药片后感到恶心头晕。他非常不喜欢这个药。
最重要的是,参与试验的医生中没有一人收集过长期使用此药对人体影响的数据。研讨会也完全没有讨论人体是如何吸收、代谢和排泄沙利度胺的。似乎没有人知道这种药在人体内是如何运作的。格吕恩泰的经理肖弗里斯特承认,把沙利度胺投入市场之前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于是公司把这种药给了另一组医生做试验,但这些试验的结果更糟。
3名在柏林执业的医生表达了严重关切。费迪南德·皮亚琴扎(Ferdinand Piacenza)医生观察到,所有参加试药的病人都全身起了皮疹,一名病人只服用了小剂量的药物就“感觉异常”(paresthesia)。他对这些副作用深感担忧,随即停止了药试。1956年3月25日,皮亚琴扎写信告诉米克特,人体对沙利度胺“绝对不耐受”。[43]米克特假装大吃一惊:“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过像你这样负面的报告。”[44]米克特在回信中解释说,公司在诊所和疗养院试验沙利度胺已有大约两年的时间(这说明格吕恩泰在长期动物实验尚未完成的1954年就私下开始了人体试药)。米克特对皮亚琴扎的担忧一笑置之,说也许他给的剂量太大了。“K17是强效镇静剂,”米克特告诫说,“一般来说小剂量就足够了。”[45]1956年,沙利度胺另一种更明显的副作用也显现出来。那年12月,在施托尔贝格附近的亚琛,格吕恩泰化学公司一名雇员的妻子产下一个女婴。几个月前,那人曾兴冲冲地把公司新发明的这种镇静灵药的样品拿回家给怀孕的妻子吃。圣诞节那天,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却没有耳朵。
沙利度胺越出名,人们的问题就越多。问题大多是关于这种药在人体内的代谢和分解的。美国的梅瑞尔公司对此也感兴趣。不幸的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数据。[46]
——格吕恩泰化学公司备忘录,1960年3月
[1] Alan Wayne Jones, “Early Drug Discovery and the Rise of 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Drug Testing and Analysis 3, no. 6 (June 2011).
[2] “Merck, the Oldest Pharma Company Turns 350,” Deutsche Welle, July 16, 2018.
[3] 著名药企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的组成部分。史克先是通过一系列合并于1989年成为史克必成(SmithKline Beecham),之后史克必成又与葛兰素威康(Glaxo Wellcome)于2000年合并为葛兰素史克。——编者注
[4] Jones, “Early Drug Discovery”.
[5] Emmanouil Magiorkinis et al., “Highlights in the History of Epilepsy: The Last 200 Years,”Epileps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2014, 582039.
[6] 又称炮弹休克,这个术语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用来描述许多士兵的战争经历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编者注
[7] Norman Ohler, Blitzed (Boston: Houghton Mi flin Harcourt, 2017), 108.
[8] “Secrets by the Thousands,” Harper’s Magazine, Oct. 1946.
[9] 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文明的发源地。——译者注
[10] Douglas M.O’Reagan, Taking Nazi Technology: Allied Exploitation of German Scienc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1), 37.
[11] F.López-Muñoz, P.García-García, and C.Alamo,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the German National Socialist Regime: I.G.Farben and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 31, no. 1 (Feb. 2009): 67–77.
[12] Jacques R.Pauwels, Big Business and Hitler (Toronto: Lorimer, 2017), 72.
[13] Jonathan B.Tucker, War of Nerves: Chemical Warfare from World War I to Al-Qaeda (New York: Anchor, 2007), 88.
[14] “German Firm Is Cited as Top Producer of Death Camp Gas,” Los Angeles Times, Dec. 4,1998.
[15] Patricia Posner, The Pharmacist of Auschwitz: The Untold Story (Surrey, UK: Crux Publishing, 2017), 61.
[16]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uschwitz camp commander and Bayer headquarters quoted in ibid., 62.
[17] 同上,61。
[18] 同上,62。
[19] 同上,64。
[20] 同上,114。
[21] Telford Taylor quoted in Scott Christianson, Fatal Airs: The Deadly History and Apocalyptic Future of Lethal Gases (New York: Praeger Press, 2010), 70.
[22] 同上。
[23]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gainst Carl Krauch et al., Military Tribunal, No. VI, C.A.No. 6,Paul M.Hebert, Dissenting Opinion, Nuremberg Trials Documents (1948).
[24] “The Nazis and Thalidomide: The Worst Drug Scandal of All Time,” Newsweek, Sept. 10,2012.
[25] Martin Johnson, Raymond G.Stokes, and Tobias Arndt, The Thalidomide Catastrophe: How It Happened, Who Was Responsible, and Why the Search for Justice Continues After More Than Six Decades (London: Onwards and Upwards, 2018), 72.
[26] “The Nazis and Thalidomide: The Worst Drug Scandal of All Time,” Newsweek, Sept. 10,2012.
[27] 莫尼卡·艾森伯格(Monika Eisenberg)和马丁·约翰逊与作者分享的他们于2009年7月在德国亚琛对克里斯蒂安·瓦格曼(Christian Wagemann)的采访。
[28] “Code K17,” Der Spiegel, June 3, 1968.
[29] “This story taxes credibility to the breaking point!” Johnson, Stokes, and Arndt, Thalidomide Catastrophe, 77–78.
[30] Johnson, Stokes, and Arndt, Thalidomide Catastrophe, 79.
[31] 同上,80。
[32] Wichmann, Koch, and Heiss, Zeitschrift für Klinische Medizin (1956), cited in Johnson,Stokes, and Arndt, Thalidomide Catastrophe, 80.
[33] 作者此处的表述不准确,肽和蛋白质都由氨基酸组成,只不过肽所含的氨基酸数量较少(有的甚至只有几个氨基酸),因此可以认为肽就是“微型蛋白质”。——编者注
[34] 作者此处表述有误,苯乙哌啶酮并不是巴比妥酸盐,两者只是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编者注
[35] “他还是精明的生意人,精明得与格吕恩泰谈成的合同规定,除了薪金外,公司还要把营业额的1%给他作为奖金。”United State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 . .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14553.
[36] 此处英文版原文为“K-17”,但作者在后文以及参考文献中都使用的是“K17”,中文版统一为“K17”。——编者注
[37] 构型指的是分子中各原子特有的固定空间排列。两种分子有可能在原子构成上完全相同,在原子空间排列之外的其他方面也完全相同,但因为构型不同,某些性质存在差异。——编者注
[38] Sunday Times Insight Team, Suf er the Children: The Story of Thalidomide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9), 28.
[39] U.S.Patent # 2830991 and UK Patent # 768821, cited in Johnson, Stokes, and Arndt,Thalidomide Catastrophe, 85.
[40] A fidavit of Michael Magazanik as to the Plaintif ’s Case Against the First Defendant, Lynette Suzanne Rowe v. Grünenthal GmbH,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at Melbourne, Common Law Division, Major Torts List, document prepared July 13, 2012, cites GRT.0001.00010.0172,a letter from Dr. Ferdinand Piacenza to Dr. Mückter, March 25, 1956, which refers to a patient who received the drug on Nov. 25, 1955. Mückter’s reply on April 3, 1956, GRT.0001.00010.0181, states that “we have been testing k17 in many clinics and various sanatoriums for about two years . . .”(hereafter Rowe v. Grünenthal A fidavit).
[41] Johnson, Stokes, and Arndt, Thalidomide Catastrophe, 82.
[42] Sunday Times Insight Team, Suf er the Children, 42.
[43] Letter from Dr. Ferdinand Piacenza to Dr. Mückter, March 25, 1956, GRT.0001.00010.0172,Rowe v. Grünenthal A fidavit.
[44] Letter from Mückter to Piacenza, April 3, 1956, GRT.0001.00010.0181, Rowe v. Grünenthal A fidavit.
[45] 同上。在其他文献中被译为“我觉得你对剂量过于热情了一些”。
[46] Sunday Times Insight Team, Suf er the Children, 100; Report for the month of March 1959 (Dr.Michael), GRT.0001.00053.0079, Rowe v. Grünenthal A fidav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