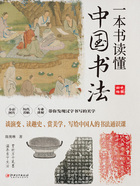
第九节 隶书发展的桥梁:三国魏碑
三国时期是汉代隶书的继续,传世作品多为隶书刻石,主要集中在当时的魏国,代表作品有《黄初残碑》《曹真残碑》《三体石经》《司马芳残碑》等。
《黄初残碑》立于三国魏黄初五年(224年)。清代乾隆初年,人们在陕西合阳发现了4块残碑,其中有一块上面有4行13个字,一块上面有2行4个字,一块上面有3行12个字,一块上面有2行6个字。这些残碑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但幸有摹本在世,令后世之人得以一睹三国魏碑的风采。
《黄初残碑》残缺得很严重,原碑的样子已难想象具体,但凭残存的字可窥见当时隶书的样貌。此碑的风格较为接近《曹全碑》,笔画秀丽,结体典雅,比《曹全碑》稍多几分古朴、浑厚之气,在端庄之外又不乏趣味。虽然用笔较细,但字势并不孱弱。在结体上,比《曹全碑》显得随意,有的字上下部首错位,有的字左右部首错位,造成重心不稳而具有别样的美感,于随意中反映出率真、自由自在的书写状态。字与字、行与行之间极显疏朗,但字散神不散。这种布局既属典型的汉碑特点,又在后世如唐、五代的碑刻中得到明显继承,由此也可得知三国魏碑在隶书石刻发展中所起到的承先启后的作用。
《曹真残碑》全称《魏镇西将军上军大将军曹真残碑并阴》,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城外,立碑时间不详,但由曹真去世时间即231年,可大体推断书刻时间。此碑被发现时只残留石碑的中部,阳面有隶书20行,每行字数少则9字,多则17字;阴面有两列题名,每列30行,每行少则2字,多则12字。此碑比《黄初残碑》时代稍晚,同样是三国魏碑中的精品。此碑藏于故宫博物院。
相对于《黄初残碑》的秀丽典雅,《曹真残碑》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整体上端庄、遒劲,既有之前汉碑中《熹平石经》的风格,又与后来北魏的石刻十分相似。在用笔上,《曹真残碑》方平、挺直,尖露锋芒,内含健劲。字体上紧凑均匀,稀疏得当,稍显匠气。布局上则十分均匀,字与字之间打着界格,可以想象这种均匀的效果正是当初作者想要的。
《三体石经》刻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年),原立于魏都洛阳南郊太学讲堂西侧。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有此名。石经内容为《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是继东汉《熹平石经》后所立的第二部石经。《三体石经》是当时经学发展的产物,早在之前已有统一经书规范的《熹平石经》,但《熹平石经》是用一种字体刻成的。《三体石经》据传由邯郸淳或嵇康等书写。此石经后迁到安阳,隋朝时迁到长安,历尽兵荒马乱,至唐贞观初年,残余部分已经不及当初的十分之一。清末和民国年间,残碑陆续在长安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曹真残碑》拓本
《三体石经》在中国书法史和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传达经学文献的同时,也是对当时三种字体的一次集体整理。就该石经书法而言,古文落落大方,篆文挺拔遒劲,隶书规范标准,因此有学者将《三体石经》比喻为集合了古文、篆书和隶书的综合大字典,为后来人们学习书法提供了参照。
《司马芳残碑》全称《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此碑未载确切的立碑年代,学者经考证,认为是三国曹魏司马懿为其父所立。此碑于1952年发现于西安,出土时只残存上半截,残余部分高106厘米,宽98厘米,正面有文字15行,共142字;阴面有14行题名,18行叙文,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司马芳残碑》的书史意义在于展现了当时隶书向楷书的转变。隶书到汉代后期开始转变,字体变得方正,有了楷书的审美特征。但是这种转变是缓慢的,起初的一些转变幅度都很小,直到《司马芳残碑》的出现。此碑虽然碑文中隶书的痕迹还很明显,但是楷书的笔意更强烈。无论用笔上的锋芒毕露、肆意又收敛,还是字体上的方平端正、大开大合,以及意境上的游刃有余,明显都是隶书和楷书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