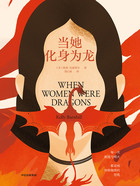
3
回顾往事,我想,母亲对姨母也怀着相似的复杂情感。她爱她的姐姐,却不尽然。母亲的身体逐渐好转,一股寒意却在二人之间蔓延开来。
“我自己来。”姨母在厨房揉面,母亲这样说;“不用麻烦你了。”姨母擦洗浴室的水泥地,母亲这样说;姨母为我编发时,母亲这样说;姨母为家具除尘时,母亲也这样说。
“我来吧,谢谢你了。”姨母读故事给我听,母亲这样说。她从姨母宽广的膝头抱起小小的我,夺走了故事书。
姨母每次叫我亚历克斯,母亲都会眯起眼睛,说:“她叫亚历山德拉。”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
屋内的气氛骤然变冷。母亲紧紧抱着我,姨母的脸色变了。“知道了。”她的声音低柔如一场无声的雪,“厨房还需要我帮忙吗?”
母亲的手臂如铁钳般箍住我。“不需要了。”她对姨母说,又补了一句,“今天谢谢你帮忙。”仿佛对方是添了麻烦的女工,马上要被扫地出门。
姨母的笑容似有若无,一闪而过,她双手插进背带裤的深兜,还在震惊之中。她瞥了一眼窗户,随即望向门。“知道了,小妹。”姨母说,“看得出来,我有点碍事。有事给我打电话。”
母亲没有回答。她只是紧紧抱着我,听着姨母的脚步声在木地板上远去,在门厅的地砖上远去。屋门猛然关上,母亲战栗了一下。
姨母第二天回来了,第三天也来了。然而,即使我还小,也嗅得出一丝变化,风暴盘踞在天空尽头,一触即发。
母亲的气色复原如初,发丝重焕光彩,力气先是如涓涓细流,而后如洪水般恢复了。但她对姨母的耐心却愈加稀薄。姨母玛拉总喜欢一次又一次地说些令人震惊的事。我听不懂内容,也不知道那些事为何令人震惊。我只知道,她说的话总是让母亲脸红。姨母也经常提到母亲的婚前生活,尤其是她的工作。姨母总是喋喋不休,讲她有多为母亲骄傲。每次谈起母亲,姨母都双手交握,容光焕发,仿佛在祈祷。相比之下,母亲却变得更加脆弱、紧绷、自闭,就像一个发条上得过紧的娃娃。
“亚历克斯,你妈妈上学的时候,在班里数一数二。”姨母总这么说,口气像是在讲童话故事,“所有人都被她甩在身后。她学数学很有天赋。天生的——”
然后,母亲就会起身离开,回到卧室,狠狠地摔上门。
二人间的摩擦酝酿了几个月,终于爆发了。盘子噼里啪啦地摔,罐子碎在水池中,张开的大手在柔软的脸颊上击出脆响。母亲懊恼地念叨着什么,姨母哭了一小会儿,房间里鸦雀无声。我躲在桌底,捂住耳朵。那天的事依然历历在目。
具体是这样的,就在姨母猛地拉开屋门,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前,母亲在门廊对着她姐姐远去的身影喊道:“等你选择了正常的生活,再回来吧。嫁个人,生个孩子,说不定我们还能和好。”
姨母没有回头。我看到她的胸膛先是剧烈起伏,随后慢慢归于平和。她望着天空,终于开口了:“好吧,我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
姨母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家中一片死寂。母亲丢给我一沓纸,让我画着玩,然后躲回自己的房间。
后来的两年,姨母没有踏足我家一步,但是依然同我们一起去教堂。姐妹二人像一对书挡,把父亲和我夹在中间,母亲穿着刺绣连衣裙,姨母穿着宽松的休闲羊毛裤和领口开到锁骨的衬衫。她是教堂中唯一穿休闲裤的女人,这对当时大多数女性来说还很出格,甚至不被教堂允许。但是姨母有种魔力,她总能让别人接受她所做的(当然,母亲除外)。毕竟,没有几个女人开过飞机,修过汽车,可是姨母这两样都做得很好。一想到这些,没有人还在乎她穿什么裤子。玛拉和我母亲戴着同款头纱,那是外祖母留下的遗物,有手织的蕾丝边和繁复美丽的图案。面纱被别在头发上,遮住她们的脸庞。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姐妹二人总是斜睨对方,试探对方的心意。
最后,姨母完全听取了母亲的意愿。她嫁了人,嫁了一个无能的醉鬼。当时我不过六岁,但也知道不该如此——主要是因为无意中听到大家都这样说。可她还是嫁了,成了别人的妻子。母亲言而有信,和姨母重归于好。
她们绝口不提那次吵架,不提那场漫长而默然的分离。她们热情相待,关系却仍旧易碎。她们脸上挂着敷衍的微笑,目光冷硬得像一对瓷娃娃。她们什么都不提。
无论如何,这些都不再重要。我四岁那年母亲消失后,她的疾病不能被提及,她归来后那事仍不能提。对面的小老太太发生了什么也不能提,至于被木板封住的房子,过路的人只是把视线避开。
然而,无论人们是否情愿,1955年的大规模化龙事件还是来了。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城市,我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将经历一场巨变。
这场巨变,也不能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