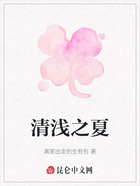
第8章 四季常青,晓英不散
晓英是李清夏家斜对面的一个奶奶,两家中间隔着一段距离的土路,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清夏奶奶的闺蜜,尤其是清夏爷爷去世之后,自己又去了县城读书,往往只能一个月回一次家,两位老人的日常来往变得更加频繁。
晓英这个名字在清夏村里是烂大街的普通存在,她不确定是不是这么写,夸张的说,一个村里多的时候会出现四五个“晓英”
“晓英对我很好啊,她隔三差五就会来找我,她怕我一个人在家孤独,每次还会带一些鸡蛋,带一些柴火。”每次回家,李清夏都要听奶奶念叨一番。
“有什么好的,她的背都直不起来,双手也是脏兮兮的,头发也总是脏成一团”,李清夏偶尔会这样嫌弃的说道,“她给的那些鸡蛋啊,我看都不想看一眼,更别说吃了”
奶奶微微一笑,“可别这么说,人家可是个好人嘞。”
听奶奶说,大概是三四十年前,晓英跟着她丈夫到村里来的,来的时候夫妇俩都穿的粗布衣裳,手里提着一个粗麻袋,里面是几件旧衣服和一口破烂的小锅,随便看上了一个没要人的屋子,丈夫修修补补,直到能简单的遮风避雨,就这么安顿了下来。
许久之后,夫妇二人就在小学门口支起了那口破烂的小锅,夏天的时候卖一些油条圆饼,冬天的时候卖一些暖胃的粥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日日如此,后来年纪大了,边上多了一把小椅子,学堂的高峰期过了,一人负责收摊,一人就坐在椅子上静静休息。
几十年来,从未涨价,无论大小,一律五毛,“涨价了,娃娃们吃不起啊,我少赚点没关系的。”每当有人嘲讽她赔本也赚不来吆喝的时候,她总是这么回答。
记得后来慢慢的,等到最后那几批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小学的孩子也越来越少,有能力的都带去城里读书了,很少会守着这些犄角旮旯了”,小学校长说道,“也好,能有父母的陪伴总是好的,过几年我也要退休喽。”
“我们的早餐摊还做吗,小学门口都没什么孩子了,你我年纪也大了,还做的动吗”晓英奶奶有一次问她丈夫。
“做啊,为什么不做,小学没有,初中不是还有一些孩子吗,人家也还是在长身体的”
清夏的小学和初中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个年纪的孩子要么住校,要么就早出晚归的骑着单车上下学。
晓英夫妇俩可不会骑单车,他们只好每天挑着担子,天不亮就得出发,但无论酷暑还是严寒,孩子们总能吃上热乎的早餐。
后来边上的人家建议,“要不就把你的锅寄存在我门口吧,放心,不会丢的啦,能减一点负担就减一点负担嘛”
但人心各异,总有几个挑事的,“孩子们,你们不要吃她的早餐啊,你看她那双满是褶子的手,这个圆饼肯定不卫生啦”
“你是什么东西,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们吃奶奶的早餐从小吃到大,干不干净用得着你说”欣慰的是,总会有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替不善言辞的晓英辩解。
清夏清楚的记得,在学到杨绛先生的《老王》那一篇课文的时候,老师问,“回想一下你们的身边,是否也有老王这样的人存在呢?”
清夏的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出了晓英的样子。“深陷在眼眶中的眼睛因为眼病变的有些浑浊,看起来时常满是泪水,满脸皱纹的皮肤饱经风霜,走路时佝偻着背,冬天的时候提着一个阿胶汤碗做成的简易火炉”
在清夏幼年的记忆里,晓英总是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在那条土路上,见到放学回家的她也总是努力的抬起头和她打招呼。
“夏夏,放学回来了啊”这是最常能听到的一句寒暄,但清夏总是视而不见。
“你怎么不理人家呢?”清夏跟奶奶提起的时候,奶奶会问。
“我喊了她奶奶好啊”估计是她耳背没听见吧。
后来,早餐摊子消失了几天,清夏回到家才知道,是晓英的丈夫去世了。
据说在她丈夫的骨灰里,发现了好几枚弹壳。
那几天早餐摊子都没有再出现,清夏弟弟和姐姐说,他每次放学回家,都能看到晓英奶奶站在自己家门口,一站就是许久,他找同学玩时,路过打招呼,她也不说话。
晓英的家,清夏小时候跟着奶奶去过一次,破败的旧式瓦房屋顶,里面是一口天井,地面是崎岖不平的泥土地,昏暗的电灯发着微光,甚至亮不过一支蜡烛。
她甚至觉得有点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从记事起到现在,只去过一次。
晓英奶奶到清夏家来,怀里总是揣着鸡蛋,她没有多余的口袋,总是用她那身黑色围裙往上一翻,就是天然的兜子。
“拿着,我家母鸡刚下的,我偷偷给你拿过来啦”有一次清夏一家人正在看电视,窗外走过一个蹒跚的人影,紧随其后的还有一些轻快的脚步声,是她的两个孙女。
她拿鸡蛋总是要避开她的儿媳,两人关系不好,她也怕被说闲话。
“留在这里吃饭吧,我多煮一点米就是了”清夏奶奶接过鸡蛋,对祖孙三人说。
但是李清夏很生气,她又不好当面说,她凑到奶奶耳朵前,“奶奶你过来,我和你说点事情”她拉着奶奶的手就往自己房间里走。
“你平时留她喝茶吃点零食点心,看看电视可以,我不反对”她关上房门就转身说道。
“但是你留她吃饭,你看她的手多脏啊,她笑起来那几颗仅剩的黄牙,她吃我就不吃了!”她说完又给弟弟使了一个眼色
“是啊,她吃我们就不吃了”弟弟跟着附和。
“你俩孩子怎么这样啊,人家平常可帮了我们家不少忙呢,你看屋檐下那一片片柴火,今天的这些鸡蛋,你们不在家的时候,全靠她和我作伴呢”
“君君女!”就在这个时候,屋外的晓英奶奶喊着奶奶的小名”,“那我就回去了啊”
“留下来吃饭吧!”奶奶赶紧跑出房门。
“不了不了,我也得回去做饭了”她带着她的两个孙女回家去了。
无一例外,每次清夏或弟弟回家,屋内看电视的热闹氛围总是会慢慢的冷下来,她估计是觉得自己不受年轻人待见,是时候该找个借口回家了。
清夏的高中是不允许带手机的,每次和家里人联系要么是借班主任的手机,要么是找门卫室阿姨的座机。
“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没有掉队吧,听班主任说,你们要文理分科了,还有分班考呢,你可得抓紧啊”电话那头的妈妈叮嘱道。
“好着呢,好着呢,奶奶最近好吗”清夏回答。
“也好着呢,你不要担心,好好读书,只是晓英走了。”母亲平淡的说。
“啊?啊!”李清夏从震惊到接受,“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上个月不是还好好的吗”
“就上个月,11月份的事情。”
“埋哪里了?”
“就埋在你小学上学路上侧边的田埂上”,“听说她家里人整理她遗物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什么特别的特等功勋章之类的”
次年二月份过年的时候,望着天空中上升绽放的烟花,清夏在唏嘘的感慨时间的飞速流逝,不经意间居然又过了一年。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她不知道晓英奶奶是如何在寒冷的11月走完了自己最终的人生,也对自己当初对她的有些无礼态度感到抱歉。
春意袭来的时候,她被弟弟拉着去小学附近的小卖部买摔炮玩,小学生就是对这种东西比较感兴趣。
她路过一座新坟,新坟的周围开始慢慢的长出绿草,周围也有点点野花环绕。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11月啊,是晓英奶奶的啊”
李清夏驻足不语,带着弟弟鞠了一躬,然后走向远方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