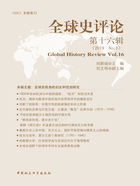
引言
关于过去30年的历史知识生产,乔·古尔迪(Jo Guldi)和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写道:“掌握档案材料;全面了解日益丰富的历史编纂;更细致的重构和分析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专业素养的标志。”[1]在他们合著的《历史学宣言》中,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反对历史学家的专业化,也就是反对“对越来越小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2]。相反,两位作者呼吁对过去进行“长时段”的研究,并主张对长期历史进程进行有意义的解读,以便思考如何解决我们一直面临的全球不平等和冲突等遗留问题。他们还竭力主张,在“长时段”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确指出、仔细探究历史转折点,并将研究建立在他们称之为“典范特例”(exemplary particular)的微观历史之上,即“历史上展现权力结构、等级和想象力的短暂时刻”[3]。
本文是“长时段”观察的一部分,观察内容是如下二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中国被纳入现代世界秩序以及在其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中国妇女的社会政治活动。本文的“典范特例”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借用丽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和彼得·扎罗(Peter Zarrow)的话说,这几年里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历史问题,这些问题自那以后对中国的现代性产生了巨大影响”[4]。
前近代帝国的扩张和解体极大地影响了权力的多层不对称,并导致了国家愿景与国际联盟之间竞争和冲突的现实。就中华帝国而言,它被强行以不利条件纳入西方世界秩序就发生在晚清时期。中国如何被对待,它被置于的位置,以及有关它对权力、社会和文化资本是如何被定义、获取和组织的这一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强加于中国并选择性内化的),自此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关系,以及中国与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在本杰明·埃尔曼(2006)关于中国现代科学的文化史一书中,他开篇就指出,对于1895年以后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和军事失败的文化叙事”应该有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永远不会取代西方帝国主义通过科学、技术和扩张得以发展的胜利叙事”。就像埃尔曼研究的“被遮蔽”的中国现代科学谱系一样,《女学报》(Chinese Girls’Progress,1898)——最早的一份“新型”报刊,声称其编辑、供稿者和读者均为妇女——所宣扬的思想和行动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在全球世界秩序中操作的这个更为不显眼的故事中有启发性的一部分。本文将对现代化进行的替代性观点进行分析,探讨中国女性如何与前近代世界与现代世界形成融合,并展望中国和中国女性的未来(当然历史并未按此发展)。
这样一来,本文不仅将参与了“算不上现代”的百日维新的妇女带入我们的议题,这些议题是关于中国被迫融入现代世界秩序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和与世界的关系,而且,通过将参与晚清社会政治的女性置于全球历史的中心。本文还致力于持续地将现代化的错综复杂历史去中心化——或如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所言的“地方化”[5]的学术努力作出贡献,并将去中心化的世界历史书写进一步性别化。
全球史、世界史、缠绕史(entangled history)、跨国史和其他类似的专业术语,在杰里·本特利看来,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些历史书写方法都具有相同的范围和分析地带,都关注“许多跨越了传统上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关注的国家、政治、文化、语言、地理和其他界限的网络体系”,本文也有同样的关注点。[6]然而,欧洲中心主义——加之美国中心主义——日益被视为之前史学编纂的一个主要缺陷,并受到挑战。正如卡林·霍夫梅斯特(Karin Hofmeester)和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所指出的,“欧洲中心主义是站在北大西洋地区的立场上对世界进行的心理秩序的划分。如此一来,最早步入‘现代’时期的是欧洲和北美,然后逐步延伸到世界其他地区”。因此,这个“核心区域”的时间性决定了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的时期划分。[7]欧洲中心主义盛行的另一种突出表现形式就是历史编纂上的疏忽,也就是作者们所关注的只是世界某一部分地区。[8]本文通过考察中国被纳入现代世界秩序、现代/现代化媒体的引入,以及晚清中国一群精英女性提出特定的(即使未实现)现代化路径的方式等三者之间的关联,希望将全球史书写的注意力从仍在运作的认识论的权力中心上转移开去。
本文展示,对全球史的审视、呈现和行动的主体并不囿于西欧—北美地区人们对“全球”这个概念的好奇、认知和积极参与,它往往体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此外,本文旨在以一种更重要的形式推动正在进行的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早在30年前,库马里·贾亚瓦德纳(Kumari Jayawardena)在对女性行动主义复杂的物质来源和意识形态来源进行开创性研究时,她就批判性地指出并驳斥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观点,即非西方女性的行动主义仅仅是对欧美“行动主义”的模仿和衍生。[9]然而,正如德·汉(de Haan)、Allen(艾伦)、普维斯(Purvis)和达斯卡洛娃(Daskalova)在其最近出版的合集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强调全世界妇女都在积极地参与社会变革的讨论和行动,这还是很有必要的。[10]本文通过强调西欧或北美之外的全球史中与性别有关的话题,也就是说,通过分析从事写作和具有“全球”视角的晚清女性的能力和信心,试图对西方英语世界的女性和女权主义学术去中心化,这种学术过分(甚至令人不安地)强调西方/“第一世界”女权主义的影响和普遍示范作用。
由此,本文将对如下问题进行分析和理论化,即《女学报》中的文本如何独树一帜地创造和利用与性别有关的国际化想象,这种国际化想象表明了中国、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现代/现代化和日益全球/全球化这样一个日益出现的地缘政治和象征等级的世界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同时,文中还会提出相关理论。本文第一部分将介绍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和政治环境,身处其中的中国女性话语性地创造了她们现代化和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第一部分还将简要介绍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想象和西方帝国的想象发生了冲突和分歧。笔者将中国晚清社会政治事件放置在现代世界等级结构的全球定位/再定位这样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框架中来思考,由此本文的论断是,正是对“文明”构成的重新定义才引发了与中国女性相关的社会焦虑,以及中国女性作为话语主体及实际的社会政治行动者的出现。
本文主体部分将仔细考察发表在《女学报》上的文章。《女学报》于上海发行,编辑和撰稿人均为女性,目标读者群也是女性。[11]尽管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分析男性作为编辑、作为以笔名发表文章的作者,以及他们作为女性报刊的读者参与其中所产生的影响,但《女学报》自称为完全由女性主导并只面向女性的媒体,因此,其刊出的内容应该是女性编辑、撰稿人和读者都关注的问题。换句话说,尽管有些话题围绕着证明报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性别问题,但是,《女学报》的读者——无论男性或女性——都认为他们读到的文章是由进步女性撰写的,其目标读者也是女性,这些女性有意致力于提升中国地位和中国妇女地位。这使得《女学报》成为专门研究至少被理解为有改革意愿的女性所从事的独有的媒体事业,这些女性作为假定的作者,就她们应该支持和承担的社会变革的方向,为假定的女性读者提出了建议。
我将《女学报》定义为向读者传播某些消息的特定媒体,读者只有以“中国读者的方式”阅读,即“从始至终,没有漏看一个字”,才能接收到其传播的信息。[12]这种阅读方式使我得以分析报刊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并非出自期刊撰稿人的个别文章。我所作的文本分析受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提出的话语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影响。[13]费尔克拉夫阐述了被视为一种作为社会行为和社会事件的话语与社会文化和政治进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借此我探究了话语实践推动的特定社会变化,这一话语实践出现在晚清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体现于现代/现代化的女性报纸之中。
此外,我采用的文本研究方法深受后殖民时期女权主义学者学术方法的影响,她们认为用交叉分析和情境分析的方法对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背景下西方和非西方问题的(话语性)相遇进行分析至关重要。对我的文本分析尤其重要的是一些女权主义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质疑存在“一个潜在统一的且具有范式意义的男性殖民主体”的假设,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女性对帝国话语定位的不同的、性别化的理解”。[14]我的文本分析方法直接受到一种批判意识的影响,即女性的观点“不能保证与他者的互动关系”[15],相反,正如诺玛·阿拉孔(Norma Alarcon)所阐述的那样,“一个女人可以通过与其他女人相对而‘成为女人’”[16]。
运用这种分析方法,我得出了与中国女性创建媒体话语的意识形态背景相关的一系列结论。我将陈述的结论是,《女学报》的撰稿人通过讨论中国女人、西方女人和非西方女人的能力、活动、抱负和成就,将中国、西方和现代/现代化世界加以叙述。正如我将要展示的那样,《女学报》中某些文章所呈现的关于女性的叙事,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赋予意义。这些文章支撑了一种历史进程的非线性时间性,把过去视为进步所处的某个时间点,这与现代西方理解的线性的、目的论的时间运动相左。这种非线性递进时间的建构与西学中源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为回归中华文明的说法提供了支撑。这一系列话语将现代/现代化的西方学识和制度看作对被忽视的中国实践的传承,这些实践从西方,经由日本,被重新引入它的源头——中国。
我将进一步论证,这些话语举措的综合运用产生了几种结果。正如我将展示的那样,《女学报》的文章既有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尊贵女性的评价,又有对外国女性的叙述。因此,我认为,将这种与性别相关的变化引入,不仅使人们了解到女性为国献功的能力和抱负(晚清女性因此得以登上政治舞台)由来已久,它还将改革描述为一种并不新鲜的东西——一种良性的、因而更可被接受的社会干预。此外,这些话语举措也可能证明,中国为了与颇具威胁性的西方势力及其推行的现代世界等级制度建立更平等的关系,付出了多少努力,有多少想象力。最后,《女学报》的文章证实了与性别相关的创造现代/现代化世界和全球/全球化世界的持续过程。结果是世界秩序被重新建构,在其中,在面对西方、面对稳固的殖民和帝国权力的逻辑,以及面对这种权力的积累和分配时,中国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