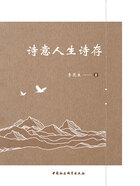
自序
出版自著诗词,曾经是我中学时代的梦想。在20世纪50年代时,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作家和诗人。但1962年高考时,我因作文题选择“论不怕鬼”,却不知道1961年2月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领衔编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只是就鬼论鬼,没有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突出论述不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国内天灾人祸这些“鬼”,致使语文成绩稍逊,未能按第一志愿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在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贸易系录取后,我的理想也就从当作家、诗人调整为做经济管理干部。在此后的岁月里,虽也吟诗填词,但那纯粹是一种时断时续的业余爱好,出版诗词的想法也就放弃了。
我的业余爱好不是很多,基本上就是读书、旅游、议论时政、吟诗填词。未曾想到,这一“业余”,在近半个世纪中,竟也积累了200余首古典诗词。丁亥春节期间,一些经济学家朋友,特别是我的学生朋友,鼓动和鼓励我出一本诗集。我思忖再三,特别是考虑到既然已经下决心65岁以后不再写经济学方面的论著,转攻文史方面的课题,选点诗词公开出来试探一下,也许有点意义。于是在2008年纪念我与老伴的红宝石婚时,曾以《潇湘斋诗词选》为名匆匆出版了一部选本。那部集子辑录的诗词不足百首。有朋友说:你那么酷爱古典诗词,怎么半个世纪才写这么点?说起来,我也确实汗颜。由于自己资质驽钝,在诸种业余爱好中,以吟诗填词最苦,成果却少之又少。客观地说,自由诗、民歌体、打油诗,甚至不拘声韵的五言、七言诗,都好写些,若写此类诗,数量肯定要多不少。但我平生对这几类诗了无兴趣,甚至偏激地认为,只有诗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才配称为“诗”,其中我最偏爱的又是唐诗宋词,认定其为诗中的珠穆朗玛峰。我早年就决定,写诗只写这样的诗。然而,由于下述两个原因,我这一辈子写的诗词数量和质量均不尽人意。
第一,我的国学功底差,学力不逮。比如,诗作的一大对象是大自然的造化神奇,我这些年去了不少中外风景名胜区,却往往是“眼前有景道不得”,主要的倒不是因为“崔颢题诗在上头”——其实在许多名胜区,前人并未留下传世名篇——而是“我愧无才状自然”。钟嵘在《诗品》中提出诗作应“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然而我却既欠风力,又缺丹彩。虽然中学时代我的语文学得不错,先师蒋炼、先师陈烈曾予谬奖;在大学时,先师王轶能也认可我的国学水平,1963年元旦曾题赠我贺卡,上书“勇猛精进”,对我勉励有加。但惭愧的是,自大学始我已移情别恋于经济学,在国学方面,我迄今仍停留于高中水平。
第二,我爱上了一种不宜我爱的诗的形式。我终生崇敬毛主席,一直以来,都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唯在写诗上与其教诲稍有不合。毛主席早在1957年1月12日致臧克家的信中就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格律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而我作为毛主席眼中的青年,却不愿学写新诗,执着地去作青年不宜的旧诗。钟嵘曾认为诗应是诗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主张“直寻”“自然英旨”“真美”,反对过分“拘于声韵”,指出“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与此相关,他还反对用典:“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写新诗完全可按钟嵘所说去做。然而,既写律诗,就得遵循非常严格的格律要求;格律诗中使用成语典故,既经济,又生动,几乎是好诗不可或缺的。写律诗是我自讨苦吃。有时尽管有了诗兴,有了创作冲动,但“拘于声韵”和想不起适用的典故,当时只得忍痛搁置,而事后一忙,也就没有再写的念头和工夫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在对欧美亚澳十余国的访问中,曾有多次触景生情,对许多情景相见恨晚,却很少写出诗词,就是如此。
任何文学作品都要求思想感情与艺术表现的完美统一,诗词尤应如此。在《诗品》中钟嵘提出诗的创作应“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他最推崇“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感情必须真实,否则最易流于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只有来自三大实践、基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感情,加上语言艺术,才能写得有“滋味”。还有,我国历来有“愤怒出诗人”之说,更有甚者,言“江山不幸诗人幸”。我并不赞同这类失之偏颇之论。我赞同诗言志、诗言情。愤怒、哀怨、悲凉,不是“志”“情”之全部。在我看来,言志的诗完全能写得非常有“滋味”;较强烈的、正确的喜与乐也都可以产生有“滋味”的诗词。上述偏颇的认识,大抵源于特定历史时代所产生的诗人创作实践:在过往的数千年中,中华民族的苦难多于康乐,在奴隶制和封建专制下,诗人的怀才不遇、颠沛流离、蒙冤受屈、贫病交加、失恋失宠等现象屡见不鲜;而外族入侵,特别是鸦片战争以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民族深受屈辱,国人饱受凌辱、蹂躏、杀戮之苦难,这些都给了诗人极其强烈的刺激,因而相对说来,这类诗词自然数量多、质量高。但这绝不意味着诗词是怒与悲的专利,而喜与乐就不能产生好的诗词。何况时代不同了,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当今之世,在中华民族振兴崛起之时,后者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诗词。我的这些诗词,就是多喜乐而少哀怨,有奋发而无颓唐,如果说自己的特色,那就是身处丛林世界和转型社会,有相当一部分则是“匕首与投枪”。虽不敢望古圣先贤诗仙词圣之项背,然跻身同辈中好此道者,庶几无愧更无悔。
关于写诗的方法,我没有正式学过,只约略知道一点,比如明白毛主席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道理,又比如粗读过钟嵘的《诗品》,知道他主张比兴赋兼用:“故诗有三义焉:一曰比,二曰兴,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但我终究知之甚少且甚为肤浅,更何况知易行难,收入这本小册子的诗词中,尽管也有些自己比较满意的,但总体看来,本诗存毕竟只是一个老中学生的习作,“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欠“词采葱倩,音韵铿锵”,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谈不上“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做不到“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聊可自慰的是,诗言志、诗言情,我做到了矢志明言、真情直抒、爱憎分明、俯仰无愧。
无论科技怎么进步,医学如何发达,我今年届八旬,毕竟已是迟暮之年,日后恐怕写不了诗了,于是清理旧作,又选出几十首加以注释,补充进《潇湘斋诗词选》,并新配能找到的旧照,形成现在这本一百三十多首的《诗意人生诗存》。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诗意人生诗存》,相较于十几年前的《潇湘斋诗词选》,虽有不少改进,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肯定还有不少问题,诚盼方家教正,在此预致谢忱。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八日——爱妻八十华诞
改定于北京望京西园潇湘二乐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