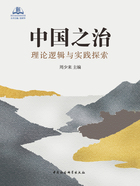
理论逻辑篇
基层治理“行为变异”之制度追问
周少来[1]
摘要:基层治理中的“行为变异”,以基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最为典型,并不断的花样翻新、屡治屡现,导致大量的体制空转、资源空耗,不但产生极高的治理成本,也严重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只有通过顶层设计的根本性制度改革,减少行政管理的权力层级,加强公共权力的民主化运行,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权能,加大对基层组织的民主监督和民主评议,巩固基层组织的自治化力量,才能使基层治理尽快走上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轨道,这才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之路。
关键词:基层治理;行为变异;制度机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之基础,是政策落实之前沿,直接关涉国家治理的效能实现和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它在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进程中十分重要。然而,在基层治理中,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为典型的各种“行为变异”屡禁不止、病根难除。2018年,中央媒体报道“直击基层治理十大痛点”,包括督查检查频繁、问责滥用、压力“甩锅”、处处留痕、材料论英雄、慵懒干部、典型速成、政策打架、上升“天花板”、幸福感缺失等种种乱象被揭露出来;[2]201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2020年,中央媒体报道“整治形式主义:老毛病反弹,新问题冒头”,并揭露出种种形式主义的新花样。[3]为什么执政党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坚决反对的“行为变异”顽固难除?为什么干部群众深恶痛绝的“行为变异”一再发生?为什么经过“减负年”运动整治的“行为变异”病根仍在?这不是高调的道德谴责、简单的现象罗列,抑或一两次集中式的“运动整治”就能完全解决,而是需要从基层“行为变异”的制度性体制机制、奖惩性激励结构和个体行为的组织逻辑等深层结构加以解剖分析。
其实,基层治理中的“行为变异”,不论是官僚主义行为,还是形式主义行为,包括基层干部的庸政懒政,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体制和组织逻辑中的“组织性行为”,也就是说是在一定的制度性激励结构和组织工作安排中表现出来的行为,虽说是体现在特定的“个体干部”身上,但其背后的行为步骤和行为走向是其组织的“组织逻辑”,是不以个体干部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他(她)在其组织制度中的“组织行为”。所以,我们对基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行为变异”的分析,就必须在制度体制—激励结构—组织行为的分析逻辑中来加以揭示,只有从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和组织逻辑中,才能深刻揭示“行为变异”的深层规定性。也只有在理解了“行为变异”的深层制度性限定,我们才能通过深层的制度性改革,从“治本”的意义上,对基层治理中的“行为变异”加以逐渐遏制和根除。否则,我们将一再落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治理循环。我们对基层治理中典型的“行为变异”,将以制度逻辑和组织逻辑的分析加以追问。
一 为什么基层官僚主义病根难除?
官僚主义,其来有自,时有泛滥,中外难免。不论是封建庄园中的官僚主义,帝制专制中的官僚主义,还是现代科层制中的官僚主义,当代中国治理中的官僚主义,虽然其表现形态各式各样,但其基本的行为特征还是长官意志、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命令主义等。为什么中央一再坚决反对的各种官僚主义,经过各种整治和教育运动,还能在基层治理中普遍长久地潜滋暗长?这就并非个别腐败官员的思想素质所能完全解释。
从制度性的体制逻辑和组织逻辑来看,第一,基层官僚主义与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紧密相关,可以说是权力高度集中体制的伴生物。权力高度集中,是中国体制的制度性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是举国体制的制度基础。但在基层,不受制约和平衡的权力集中,加之权力运行的制度化法治化薄弱,权力高度集中在某一位“官僚”手中,往往会导致高高在上的权力任性和命令主义。邓小平当年批判官僚主义时,就深刻指出,权力高度集中体制“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4]这也是目前基层官僚主义难以根治的总根源。第二,基层官僚主义与压力型体制紧密相关,可以说是压力型体制的副产品。压力型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党政任务贯彻执行的基本体制机制,是通过把项目任务层层分解、层层落实和层层检查来保证贯彻执行的方式。[5]在当前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各种工程任务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和压力大,各种层层加码、层层督查的命令主义和长官意志,就通过压力型体制沿着权力链条而传导到基层组织。第三,基层官僚主义是其部门职权和职能下传的表现和方式,各个上级职能部门,如县级的组织部、宣传部、农林局、环保局、卫健委、扶贫办、维稳办等几十个职能部门,把本该由其领导和部门负责的各种工程任务,通过压力型体制的“条块管理”,分解下传到各个乡镇政府,同时把其领导的长官意志和部门指标下传下去。这样既可以保证其所管理的任务按期完成,还可以把其负责的责任同时下传下去,以便把其部门权力最大化和责任最小化。第四,基层官僚主义与其权力运行的监督薄弱有关。由于基层官僚主义都是“有权者”的权力任性,下级组织和干部不敢监督也无法监督,更上级的组织有权监督,但由于“鞭长莫及”而监督不到位。如县级职能部门的官僚主义,乡镇政府根本不敢监督,因为各个职能部门都掌握着乡镇政府的资源分配权和考核评比权。第五,基层官僚主义是一种“组织行为”,官僚主义虽然体现在个别领导的意志和行为中,然而是在其领导工作的组织行为中隐藏着,是“领导”为了工作任务的完成而加以体现的,甚至往往把领导的官僚主义体现在各种红头文件和项目责任书中。下级领导反抗上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往往会被定性为反抗上级组织的“政治纪律”问题。
二 为什么基层形式主义反复泛滥?
从制度关联上看,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紧密相关,上有官僚主义严重,下有形式主义泛滥,形式主义是应对官僚主义的无奈手段。从形式主义的表现来看,花样繁多、形式翻新,有显性的形式主义、有隐形的形式主义,有会议形式主义、有文件传达形式主义、有填表形式主义、有台账形式主义,有传统形式主义,也有“新马甲”的电子形式主义。对于各种形式主义,上下共愤、官民共怒,为什么在基层还是反复发生?
第一,基层形式主义是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反应”,从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到基层乡镇政府,上级的每一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有权力和项目可以下传给基层组织,同时都有权力随时到基层检查监督。基层政府的权小、人少、事多,项目任务不堪其负,检查监督应接不暇。一个中部乡镇,每年要接待150多个检查监督组,要填写几百种数据台账,要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从形式上“完成”上面交办的各项任务,重压之下的基层形式主义“匆忙应对”,就是基层组织的“正常反应”。第二,基层形式主义(工作)成为基层组织的“工作常态”,一个基层乡镇政府,一年有几百个会议要到县里参加,一年有几百个检查组要接待陪同,一年有几百种数据资料要报送,一年有几十项工程任务要落实,一年有几十个村组要走访调研等。基层干部深陷形式主义工作泥潭而不能自拔,难以积极主动的开展工作和走访群众。第三,基层形式主义工作往往是“组织行为”,个人无力抗拒而必须服从。各种参会要求、文件传达、任务分解、指标量化、资料报送和数据填报等,都是通过组织文件、组织会议和组织通知,下传给基层组织和干部,基层干部得忙于参加会议、传达文件、填表报送等,也是组织安排的工作。一是个别干部无力抗拒,组织安排的工作与个人的职位和工资直接挂钩,抗拒组织安排的工作,就等于抗拒组织,从而断送自己的前程。二是各种基层形式主义“空耗”,花费的是公共成本,一个村庄一周打印了3000多页资料,花费的也是“村里的钱”,而要抗拒形式主义,个人是要付出自己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而且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性。所以,对于基层形式主义,人人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那就只有以基层形式主义,不断应对来自上面的形式主义要求和官僚主义指令。这是基层形式主义,人人喊打而人人从之的制度根源,也是基层形式主义反复难治的制度根源。这其实与基层干部的思想素质并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把一个从道德上极力谴责形式主义的人,放在乡镇政府工作一年,也不得不学会各种“形式主义应对了”。
三 为什么“层层传递压力和责任”成为基层工作机制?
基层组织为什么“压力山大”?为什么成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各种“行为变异”的重灾区?这与基层组织(县乡组织)开展工作的日常机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相关。
从体制层级来分,可以分为两个层级,一个是上级各种组织与基层组织(县级组织)的权力关系,中央、省、市的各项政策和任务的落实和下传,一般都是布置到县级组织。县级党政组织作为治理一方的基层政权,负有本县域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等各种责任。当然,中央的各位部委、省、市的各种职能部门,也有权力直接深入基层乡镇,检查监督本部门所负责工作的进度和质量,这也是乡镇政府迎接上级各个职能部门检查之多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是基层政权内部的工作机制,也就是县—乡镇—村社的工作机制。县级政府及其各个党政职能部门,把接到的上级政府的各项任务和本级政府的规划安排,再通过召开会议—分解任务—签订责任书这一程序,下传到各个乡镇政府。乡镇政府最终成为了各项项目任务的最后实施者和落实者。通过各种项目任务的责任书签订,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力运转的实现机制:一是通过层层加码的项目责任书,把县级职能部门的项目压力下传给乡镇政府,减少本部门的党政压力和任务压力,并确保其所负责任务的按期完成。二是通过层层加码的项目责任书,把本部门所负责的项目责任,顺着任务下传的同时,“搭便车”式的下传给乡镇政府。一旦项目完成中出现任何问题和责任事故,可以第一时间下查乡镇政府的组织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县级各种项目责任书,都是与乡镇政府的书记或乡镇长直接签订的原因。这也造成了乡镇政府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同样沿着权力链条,把乡镇政府的压力和责任,通过与各个村社组织的领导人签订责任书,同样进一步下传到村社自治组织之中。这便是目前全国各地普遍推行村社自治组织行政化管理、行政化考核,并与村社干部的工作奖金直接挂钩的制度性原因。甚至在全国的一些地方,行政村组织还对其下的村民小组长,也进行同样的行政化管理和考核,并与其工资补贴挂钩。
四 为什么对基层的督查考核如此之多?
面向基层组织的督查考核之多之频繁,已经成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最大烦恼,并且已经从党政机关扩展到国企单位、事业单位和各级学校。为什么各级组织热衷于对下级组织进行督查考核呢?这是由压力型体制的“工作机制”所决定:上级组织召开会议—分解任务量化指标—签订项目任务责任书—督查考核评比。各级体制内组织都已陷入了这一“工作机制”的忙乱循环之中。无论哪一级组织,都面临着督查考核下级组织,同时又被上级组织督查考核。所以,各级组织都“显得很忙乱”,都在应付上级的督查考核,只不过“匆忙应对”式的形式主义和“行为变异”,在基层组织表现得更加集中和明显而已。
对于上级组织而言,对下级组织布置完任务和签订好责任书之后,其部门自身的主要工作就剩下“督查考核”了。这对督查考核者有以下组织利益:其一,部门权力最大化,每一个组织部门都有其自身的职责和权力,在层层传导压力的体制下,各级组织普遍信奉“有为才有位”的权力逻辑,极力把本部门的权力最大化运用。不断扩张本部门的“管理权限”,制定不断细化的“管理规则”,而这些规则规定的实施都需要不断地督查考核。其二,部门利益最大化,督查考核者也面临着自己上级组织的督查考核,而考核的内容也是“召开了多少会议,出台了多少文件、开展了多少督查(对下级)、有多少数据台账”等,这些考核成绩与本部门的奖金和福利、甚至与部门领导的升迁相挂钩。这也促成了各个职能部门竞相开展“管理竞赛”:规则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细化。其三,把本部门的任务和责任下传到下级组织,如县级的环保局和维稳办,通过“属地化管理”原则,把自身的部门职责,通过签订责任书,分解下传到各个乡镇。一方面,可以表明本部门的政治态度和执行有力,增加自己的考核成绩;另一方面,一旦发生任务问题和事故,都可以追查基层乡镇的责任。
对于下级组织,作为被督查考核者,第一,没有任何抗拒任务和督查的权利,因为无论哪一级的上级政府和其职能部门,都掌握着对基层组织的资源分配权和督查考核权,都直接关系到基层乡镇的政绩和利益,甚至直接与个人的工资福利和晋升前途相关。第二,基层乡镇面对众多的“婆婆”,是众多督查考核的“汇集点”。中央的几十个部委、省级的几十个职能部门、市级的几十个职能部门、县级的几十个职能部门,哪个部门都有直接到基层乡镇督查考核的权利。一个基层乡镇一年接待几百个督查考核组,填报几百项数据台账,出现众多的形式主义“行为变异”,也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第三,因为任何的督查考核,都直接关系到基层乡镇的组织政绩和干部利益,乡镇政府都必须“圆满完成”“百分之百完成”。“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因此,“表面上完成”“数据上完成”“材料上完成”“注水式完成”“造假式完成”等必然出现。同时,也造成了乡镇政府把任务和责任进一步“下卸”到村社自治组织的趋势,形成日益严重的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
五 为什么基层干部最容易出现“行为变异”现象?
外界压力越大,物体越容易变形,人亦如此。基层干部作为任务落实的最前沿、矛盾问题的第一线,处于“上下夹击”的尴尬夹层。近年来所受到的“压力山大”已成为社会共识:任务繁多、迎检频繁、权力有限、资源不足、无奈“背锅”、角色紊乱、前景无望、有怨无声、疲于应付等。但基层干部作为一个最大的“干部群体”,其内部各层所受的压力也各有不同,这与其各自的“仕途预期”和“行为激励”有关。
乡镇主要领导,包括乡镇书记、乡镇长、副书记、副乡镇长,由于现任的主要领导,大部分都是由县直机关或本县外乡镇调任过来,如果年轻有为,有很大的晋升空间,则会对乡镇工作拼命努力。同时,这些年轻领导,也会对本乡镇的其他干部施加很大的任务压力,以期本乡镇工作在考核评级中取得最好的成绩(很多基层考核实行“末位淘汰”的惩罚机制)。虽然主要领导也是“压力山大”、负重前行,但为了把本乡镇的各项工作和任务都做到“圆满完成”,则往往造成很多“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甚至出现各种形式主义的“应付造假”。
乡镇的一般干部,特别是年龄偏大、晋升无望的干部,往往是“忙于应付”“被动工作”,甚至“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不出现任何问题和漏洞,自身的工作只是“吃饭的饭碗”。这也是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庸政懒政”的原因,“激励机制”不足是工作应付被动的制度原因。
乡镇中的新进干部和大学生选调生,如果是本地的年轻干部,发现自己还有很大的晋升前景,则会努力围绕主要领导积极工作。如果是外地来的大学生,在本乡镇无亲无故,也没有多少晋升前景,则更多地把现任工作当作临时性的“跳板”,会在短期内通过“考研”或“辞职”离开基层。这是目前基层年轻干部队伍不稳定的根源。
村社(行政村和社区)干部,作为自治组织的成员,本应该代表自治组织的利益和意见。但由于目前不断下延的“行政化”趋势,对村社干部的管理和考评,基本上与对乡镇干部的管理和考评一样的标准,并直接与村社干部的工资福利挂钩。村社干部也都在忙于各种填表、收集资料和报送材料。一个村社自治组织,往往要做几十项台账资料和报送近百项数据统计。[6]
基层干部出现各种“行为变异”,自然是“压力所致”,虽然是“深恶痛绝”,但也“无可奈何”,既无权利也无能力加以改变。同时,由于基层干部都在“忙于应付”,更无多少时间和精力,进行积极主动的创新和改革,基层干部创新担当、干事创业的活力和空间处于极大的阻滞状态。
基层治理中的“行为变异”,以基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最为典型,并不断地花样翻新、屡治屡现,导致了大量的体制空转和资源空耗,不但引发极高的治理成本,也严重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只有通过顶层设计的根本性制度改革,减少行政管理的权力层级,加强公共权力的民主化运行,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权能,加大对基层组织的民主监督和民主评议,巩固基层组织的自治化力量,开放社会舆论和社会组织的监督渠道,才能使基层治理尽快走上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轨道,这才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之路。
[1] 周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2] 《直击基层治理十大痛点,你对哪个感触最深?》,《半月谈》2018年第24期。
[3] 人民网联合报道组:《整治形式主义:老毛病反弹,新问题冒头》,人民网,2020年9月1日,vnn.people.com.cn/GB/nl/2020/0901/c14717-31844064,html?ivk_sa=1024320u。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5] 荣敬本、崔之元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4页。
[6] 人民网联合报道组:《整治形式主义:老毛病反弹,新问题冒头》,人民网,2020年9月1日,vnn.people.com.cn/GB/nl/2020/0901/c14717-31844064,html?ivk_sa=102432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