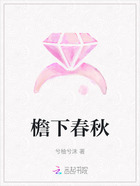
第3章 黔州雨痕
从江南回到黔州已三月有余,老房子的青瓦上爬满了秋苔,像被谁铺了层揉皱的绿绢。九月的风裹着桂花香钻进幼儿园,我蹲在秋千旁给孩子们系围巾,忽然听见新来的陈老师说:“前街来了批画古建筑的外地人,领头那个穿深灰风衣的,长得真像画里的人。“
手中的毛线围巾突然滑落,我望着操场上的梧桐叶,想起沈砚之在古戏楼二楼临窗调茶时的侧脸——那时他穿藏青改良长衫,腕间银镯轻晃,茶盏里浮着片新鲜银杏叶。自七月离别后,我们像两片漂向不同方向的银杏叶,偶尔在微信里分享天气:他说桂花开了,我回他雨落了,话题总在“古建修缮“和“孩子趣事“间打转,像被精心装裱的信笺,工整得让人不敢拆封。
周末应朋友之约去黔州老城,木簪子别住被秋雨打湿的碎发,帆布包里装着给孩子们捡的梧桐叶。巷口的糖画摊飘来甜香,恍惚间竟与江南的记忆重叠,我慌忙低头看手机,却在抬头时,看见街角穿深灰风衣的身影——藏青围巾、银镯轻晃,是沈砚之。
他正与同行的人站在雕花门楼前,指尖抚过门楣上的蝙蝠纹,动作像在触碰古戏楼的雕梁。我攥紧帆布包带,喉咙发紧。朋友忽然拽住我:“苏郁,发什么呆?这家酸汤鱼超好吃!“等我再抬头,巷口已只剩穿蓝布衫的老人,推着卖米糕的小车缓缓走过。
“可能是错觉吧。“我对自己说,跟着朋友拐进石板巷。可路过染布坊时,却鬼使神差地回头——沈砚之站在三丈外的石桥上,正举着相机拍飞檐,深灰风衣被秋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的藏青立领衬衫。那是在江南时我常见的穿搭,此刻在黔州的秋阳里,竟像幅水墨长卷里的留白。
“苏郁!“朋友的叫声惊飞了檐角的麻雀,等我再望过去,石桥上只剩三三两两的游客。染布坊的老板娘正在收蓝印花布,布料上的并蒂莲被风吹得飘起来,像极了沈砚之刻刀下的牡丹。我摸出手机,想发句“你在黔州?“却终究按灭屏幕,将梧桐叶夹进笔记本。
三天后的周六,我在超市绘本区挑拣临期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书脊上的兔子先生缺了只耳朵,像极了沈砚之送我的那片带虫蛀的银杏叶。忽然听见扶梯上传来交谈声:“砚之,你们搞古建的,是不是看什么都是榫卯结构?“
心脏猛地漏跳半拍。这声“砚之“太像古戏楼里老人的呼唤——那时他正蹲在后巷修补石斛花枝,阳光穿过藤蔓在他眉骨疤痕上织金。我抬头,看见沈砚之站在扶梯中段,深灰风衣衬得肩背愈发挺拔,腕间银镯随扶栏的动作轻晃,在商场暖黄的灯光下划出细碎的银光。他正与同行的男人说话,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银镯边缘,忽然侧头,目光精准地撞上我——像在古戏楼二楼初次相遇时,他转身看见茶盏旁的我那样自然。
“苏老师!“他迈下扶梯的皮鞋声,像敲在我心上的鼓点。近了才看见,他领口别着枚木质胸针,雕着半开的牡丹,正是古戏台上的纹样。“怎么在这儿?“我攥紧篮柄,听见自己的声音发紧,像被秋雨淋湿的琴弦。他扫过我购物篮里的蜡笔,嘴角微扬:“来出差,做古建筑调研。“
他身后的男人挤眼:“砚之,不介绍一下?藏得够深啊。““苏郁,之前在古戏楼见过。“沈砚之耳尖微泛红,却仍温文尔雅,“这是我同事,陈默。“陈默伸手要接购物篮:“苏老师当幼师?我侄女就爱粘着漂亮老师,快让我巴结下。“我后退半步,蜡笔滚落在沈砚之脚边,他弯腰捡起时,指尖抚过卡通图案:“草莓味?“
“孩子们总偷着闻。“我接过蜡笔,触到他掌心的温度——比江南的秋雨暖些,像黔州冬天的炭盆,隔着棉手套仍能感到灼意。陈默忽然指着我帆布包:“这刺绣是苗绣吧?砚之,你不是在做黔州古建筑调研吗?快让苏老师给你讲讲。“
餐厅落地窗外飘着细雨,陈默絮絮叨叨说着设计院趣事,沈砚之偶尔插两句,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目光时不时落在我腕间的银镯子上——那是奶奶留下的老物件,刻着缠枝纹,与他的银镯遥相呼应。
“黔州的吊脚楼多是穿斗式木构。“我指着沈砚之递来的调研报告,指尖划过他画的问号,“但年轻人外出打工,老房子缺人修缮,很多都快塌了。“他听得极认真,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阳光穿过他睫毛,在眼下投出细小的影。陈默忽然笑出声:“你俩一个画,一个讲,干脆组个'古建护卫队'得了。“
暴雨突至时,我们正走到商场门口。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幕墙上,陈默的手机突然震动,他接起电话后脸色微变:“项目出了点问题,我得赶回设计院。“临走前冲我抱歉地笑,“苏老师,麻烦帮我照看一下砚之,他最近为了赶调研进度,总顾不上吃饭。“
餐厅里只剩我和沈砚之相对而坐。他面前的牛排只切了两刀,沙拉几乎未动,我这才注意到他眼底的青黑——像古戏台上久未修缮的雕梁,带着岁月侵蚀的痕迹。“你……没好好吃饭?“我问。他低头用刀叉拨弄冷掉的蔬菜,银镯在腕间晃出细响:“调研周期紧,每天只来得及啃个面包。“
出租车在雨夜里穿行时,他忽然身子一歪,额头重重磕在我肩上,喉间溢出压抑的闷哼。我摸到他颈间黏腻的冷汗,衬衫下的肩胛骨硌得掌心发疼:“沈砚之?“他颤抖着从公文包摸出小铁盒,却因指尖无力而滑落。我慌忙捡起薄荷糖塞进他嘴里,指腹擦过他额角时,触到道浅淡的凸起——那是道藏在发间的旧疤,像道细瘦的月牙。
我的指尖顿在他眉骨上方,目光不由自主地凝在那道疤痕上。他忽然抓住我手腕,银镯滑到手肘,露出腕间新月形疤痕:“十岁那年,偷爬戏楼雕梁想刻牡丹,摔下来时刮到台角铜铃。“他哑着嗓子开口,气息灼热喷在我耳后,“缝针时攥着半朵木雕不肯哭,爷爷说,戏文里的好汉都得带点伤。“
急诊室的灯光下,他的脸色苍白如纸,却仍攥着我的手不放:“别担心,习惯了……“我望着他眉骨下淡色的纹路,忽然想起古戏楼后巷那株被他修补的石斛——伤痕与新生,都在时光里生了根。
雨停时已近午夜,南明河的水面漂着碎银般的月光。我陪着沈砚之走出医院,他将伞往我这边倾了倾,自己半边身子浸在雨里。急诊室惨白的灯光还在眼前晃,我望着他腕间松散的袖口,忽然想起他后颈沾着的冷汗——那里本该被藏青立领遮住的。
“以后别总啃面包。”我攥着他给的戏院子季票,信封边角硌得掌心发疼,“古建修缮要爬高上低,低血糖太危险。”他垂眸看我,睫毛在眼下投出细碎的影,像古戏楼窗棂上的冰裂纹。“知道了。”他忽然伸手替我拢了拢被雨丝打湿的碎发,银镯轻晃间掠过我耳尖,“小时候饿肚子刻木雕,爷爷总说‘榫卯要严丝合缝,人也要吃热乎饭’。”
三天后,室友收拾书柜时不小心碰倒花瓶,那枚银杏书签被水浸得开裂。我盯着碎成两半的叶片,喉咙突然发紧——叶脉间的虫蛀痕迹是他故意挑的,边缘的银线是他用刻刀一点点磨出来的。站在老城巷口,阳光穿过裂缝在掌心织出残碎的光影,我不敢细看那道裂痕,仿佛每道纹路都在提醒我,有些东西破碎了就再也回不到原样。
染布坊老板娘的话混着蝉鸣钻进耳朵:“修竹木的手艺人?往石桥方向走……”我攥着书签碎片起身,裙摆扫过青石板上的苔藓。雕花门楼前,沈砚之正俯身盯着老银匠手中的錾子,深灰风衣下摆落在潮湿的石板上。他指尖悬在半空中,似在临摹匠人修补木构件的手法,金粉从指缝间滑落,洒在他鞋尖的银杏叶纹路旁。我停在三步外,看他眉骨下的旧疤被阳光镀上金边,忽然想起急诊室里他攥着我手时,那声压抑的闷哼。
“苏郁?”他听见脚步声时回头,眼中闪过惊讶,仿佛没想到会在此处遇见我。我这才注意到他脚边摊开的笔记本,页面上画着老银匠工作台的速写,角落标注着“嵌银工艺在古建修复中的应用”。他唇角微扬,指腹敲了敲笔记本:“在做传统工艺调研,这老银匠的嵌银手法……”话音未落,便被我慌忙藏到身后的手打断。
他目光凝在我攥紧的拳头上,眉心微蹙:“手怎么了?”喉间像塞了团浸水的棉絮,我摇头时发梢扫过脸颊,触到一片湿热——原来不知不觉间,眼眶早已发烫。他忽然起身,风衣带起的风拂过我手背,惊觉我正发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伸手要碰我肩膀,又在半空顿住,指尖虚悬着,像触碰易碎的古建构件。
我低头递出书签碎片,碎片边缘的银线刮过掌心,疼得我本能缩手。他瞳孔猛地缩紧,接过时动作极轻,仿佛在触碰一件濒临失传的古物。阳光穿过他指缝,落在裂痕处,他喉结滚动着,指腹反复摩挲开裂的叶脉——那是他曾用放大镜细细观察过的纹路,此刻却成了我心底的缺口。
“我带回去试试。”他忽然开口,将碎片小心放进随身的帆布包,银镯轻晃间碰响包带扣,“老银匠的嵌银需要三天,你……别担心。”他抬头看我,目光掠过我泛红的眼角,耳尖微微发烫,“修古建的人,最懂怎么让破碎的东西重生。”
我望着他攥着包带的手,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忽然想起他修补古戏楼雕梁时的模样——总是那样专注,仿佛在缝合时光的伤口。“好。”我轻声说,声音里带着连自己都惊讶的哽咽,“我相信你。”
三日后,手机屏幕亮起沈砚之的消息时,我正给孩子们讲绘本。“书签修好了。”短短五个字让指尖发烫,我匆匆放下绘本往操场跑,半途被陈老师拽住:“苏老师快看,门口站着个风衣帅哥,正往咱们这儿看呢!”她扒着走廊栏杆往下指,语气里带着八卦的笑,“你说他是不是在等女朋友?”
我喉咙动了动,却没出声。目光越过她肩头,看见幼儿园铁栅栏外,沈砚之撑着伞立在梧桐树下,深灰风衣被秋雨洇得发暗,手里提着个蓝印花布裹的纸包。他的目光正掠过操场,扫过秋千架时顿了顿,像是在辨认哪个是我常坐的木凳。雨滴顺着伞骨滑落,在他脚边积成小水洼,倒映着他微微蹙起的眉心。
**他像站在光里的人,而我不过是青苔上的影子。**陈老师的调侃在耳侧模糊成雨声,我望着他鞋尖沾着的泥痕——那是奔走古建间的印记,而我的鞋边永远沾着幼儿园的粉笔灰。我们就像书签上的裂痕与银线,看似咬合,实则隔着破碎与重生的距离。
陈老师的声音渐渐模糊,我轻轻挣开她的手,沿着楼梯一步步往下走。鞋底蹭过台阶的声音混着雨声,心跳声却格外清晰。他看见我时,指尖轻轻收紧了纸包,伞骨在风里晃出细响。
“嵌银线时走了点神。”他隔着栅栏将纸包递给我,指腹蹭过我掌心时迅速收回,“不过……应该能看。”我接过时触到他指尖的温度,像古戏楼檐角的铜铃,在秋风里轻轻震颤。拆开的瞬间,金粉混着木料清香扑面而来,那道裂痕被银线勾勒成流水纹样,叶脉间的金箔像碎掉的月光。
他指尖虚悬在书签上方,欲言又止:“修补古建讲究‘最小干预’,所以……”“很好看。”我轻声说,喉咙发紧。抬头时撞进他的目光,睫毛上的雨珠折射着光,像他笔记本里未画完的星子。可星子终究在天上,而我只配拾捡落在泥里的月光。
陈老师领着孩子们从二楼探出头,不知谁喊了句“苏老师有个穿风衣的朋友”,惹得小家伙们拍着玻璃起哄。沈砚之冲孩子们微微颔首。我攥着书签的手轻轻发抖,忽然想起他在雕花门楼前临摹银匠手法的模样——此刻的他,比任何古建构件都更让我心动,却也更让我清楚,我们之间横亘着整个烟火与月光的世界。
“我该走了。”他忽然退后两步,风衣在风里扬起一角,露出藏青立领下的锁骨。我看着他转身的背影,忽然伸手拽住他一片衣角,又像被烫到般迅速收回:“谢谢你……修补书签。”他顿住,却没回头,只从口袋摸出片新刻的银杏叶,轻轻放在我掌心:“苗寨的吊脚楼,刻着玩的。”
雨丝落在书签的金箔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我望着他消失的街角,掌心的银杏叶叶脉分明,朱砂勾勒的吊脚楼像枚小小的印章,盖在我潮湿的掌纹里。陈老师不知何时走到我身边,她的目光从沈砚之消失的方向收回,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里带着洞悉的温柔:“有些故事啊,就像这秋雨,看着湿了衣裳,实则早就润到心尖儿里了。”
**可心尖的湿润终会风干,就像他鞋尖的泥痕会被雨水冲刷,我袖口的梧桐叶终将碾作尘埃。**幼儿园的梧桐叶还在落,有片叶子恰好跌进我袖口。我忽然明白,有些心事不必说破,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是照亮人间的月光,而我是仰望着月光生长的苔藓——虽在同一方天地,却永远隔着光与影的距离。
原来有些故事,从相遇时就写好了注脚。就像他修补的书签,裂痕里藏着的温柔,是时光给孤独灵魂的馈赠,却不是终将圆满的预言。而我能做的,不过是将这片带着金缮的叶子夹进教案本,在每个落雨的午后,轻轻翻出那道银线,告诉自己:曾有月光路过我的窗台,即便终要走向各自的归途,那瞬间的照耀,已是命运最慷慨的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