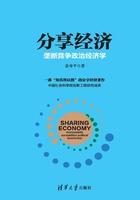
1.1 分享经济利益论的议题设置
1.1.1 如何提出利益问题:回到李嘉图
分享经济的问题分为利益与资源两个方面,其中,利益问题在展开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对元问题进行如下设问:利益问题应该如何提出,或者说分享经济理论的利益论的议题应如何设置,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如果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本能的反应很可能是提出如下见解,比如,通过分享,人们会得到出行方便、消费便利、物尽其用等好处。深入一点儿想,也无非想到,分享使生产要素更为有效配置,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等。
实际上,解析利益问题在理论经济学的根部,有两个重大的分叉,在分享经济研究上都会表现出来。一是从新古典主义的生产要素分配论角度;二是从古典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利益相互作用(社会关系) 的角度。上面提出的问题,不能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但角度却忽略了内生社会关系,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基础上一开始就走偏。
的角度。上面提出的问题,不能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但角度却忽略了内生社会关系,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基础上一开始就走偏。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分享经济,不同于研究闲置资源利用的角度在于,它从利益相互作用而非资源配置角度切入问题。它研究谁将从分享经济中受益或受损,应该如何分配分享所得利益,谁最应支持或反对分享经济,为什么要支持或反对。
理论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按其侧重重心在资源配置与利益相互作用的不同可分为两类。前者可称为斯密问题,后者可称为李嘉图问题。以斯密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马歇尔以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李嘉图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古典经济学类型的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
对分享经济来说,闲置资源利用,主要是一个斯密问题(配置问题,即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最关心的是资源如何能够实现最优配置,通过利用闲置资源,在不改变生产关系条件下做大蛋糕;使用而非拥有,主要是一个李嘉图问题(利益问题,即主体与主体关系问题),最关心的则是谁能从分享中得到最大利益,通过使用而非拥有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分好蛋糕。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使用而非拥有”与工业化时代的所有权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按照海洋法系的财产观,资源不使用就是浪费;但按大陆法系的财产观,拥有者具有可以合法浪费的权利,分享经济应如何看待财产呢?搞分享经济连产权都搞不明白,一旦深入研究就会迷失方向。
当前分享经济的议题,更多是从资源配置角度设置的,但本项目的第一阶段研究则主要从利益相互作用角度设置议题。由于李嘉图一直强调利益相互作用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称这种议题设置为“回到李嘉图”。但有别于李嘉图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分享经济的基础理论需要发展为内生技术的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或简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 )。
)。
如何设置分享经济的议题,与如何看待利益的性质有关。认为利益是物,方法就会倾向于经济“物理”学(接近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方法),把利益视为单纯的资源配置问题;如果认为利益是社会关系,方法就会倾向于经济“分配”学(接近社会科学中的以人为本方法)。后者倾向于把利益理解为人与人之间权利互动的结果,把经济理解为争夺利益份额的斗争。心物一元的观点进而认为,人与人的社会互动(分配蛋糕)与资源配置(做大蛋糕),二者将在相互转化中统一于广义均衡(内生利益相互作用的均衡)。
从利益关系角度认识分享经济,首先应回到这个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即李嘉图问题。李嘉图认为,利益分配是政治经济学(有别于斯密)的核心问题。工业化时代,利益相互作用表现为利益在土地所有者、资本拥有者和劳动者“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他说:“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9CDA8E/8171499304993501/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9697984-mw82z6vTHy1pVWu9VSksHGqpCimF8YiQ-0-7246f0f078240ef37ed749f7a2becfeb)
对分享经济来说,这种分配不光是生活条件的分配(协同消费),更是生产条件的分配,即生产资料拥有权、使用权的分配(如租值分成)。分配的核心是价值问题。这里的价值有所特指,劳动价值论所说价值,在其古典含义中,含有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价值,而不是资源配置决定价值的意思。在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实际也是一种价值现象,它是有“社会”才具有,而在鲁滨逊状态下则没有的现象。这样的价值体系与斯密的供求价格体系,是相反的体系。这两个体系的相反相成,指向了本研究中所指的垄断竞争状态。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甚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无论左右,在这一点上都相对一致。例如,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从根上否定效用函数这一概念。理由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一样,都在诟病效用函数表现不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往轻里说叫利益博弈,往重里说叫阶级斗争)。因为效用最大化,没指明生产方中哪个要素主体获得利益多,哪个获得利益少。新古典理论预设其中没有利益矛盾(即零摩擦条件下不合“理”的利益相互抵消,因此不发生我们有所特指的“相互作用”),其实矛盾是有的,经济中的刚性客观存在,很大部分就来源于此。分享,表面上是资源分配,背后却是利益分配。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有着现实依据。对利益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基础理论上的说法,遇到实际问题,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甚至上层建筑,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不适应现象。比如,对网约车治理来说,有政府部门可能就会认为,只有顺风车才算分享,而约租车因为有利益回报因此不算分享。可见,这个问题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因现实问题引起的,与具体规制对应的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利益理论,还没有在所有的地方讲通。再比如,按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使用而非拥有”不能成立,因为资源归属于我,利用还是不利用(甚至浪费),拥有者具有随意支配权(滥用权),滥用资源并不违法。分享经济虽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在关于利益的权利法理上,于法无依。可见,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钻书袋,而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已火烧眉毛的实际问题。
1.1.2 如何解析利益问题:技术、制度与均衡
针对现实,分享经济理论在利益相互作用方面回答的是下述问题:分享经济赢利是否有正当合法的权利作为依据?分享资源和财产,将对利益关系产生何种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影响(例如分享如果不姓社也不姓资,姓什么)?分享引起的经济和制度上的连锁反应,与技术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古代的分享与互联网分享有何不同)?等等。
标准经济学假定人的利益是围绕最大化(实质是两权一体化下以支配权为中心)而达成一致的,而政治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认为这种最大化中存在利益冲突这种利益相互作用,这种冲突导致最大化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社会关系冲突导致摩擦),需要用适当的制度设计,在付出一定交易费用后平衡这种矛盾。
分享经济特殊在拥有与使用两权分离,“使用而非拥有”。需要通过支配权的利益与使用权的利益相互作用达成合约解决矛盾。此前,在工业化中,两权冲突不明显,经理人与工人享有的都不是充分的使用权(只是受雇者;受雇者不具有与独立使用权对应的分成收益权),而未来的分享经济的利益关系更像历史上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各自拥有部分生产资料,双方分成),当一线劳动者的“资本”(知本)比重超过拥有者时(例如C2B,即消费者到企业),危机发生。平台“垄断”租金(假设不仅是闲置而是无限可复用)与双创的分成比例应如何确定,成为分享经济亟待研究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超出了原有的理论的最大边界,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分享经济的解释力都会骤然下降。为了在分享经济问题上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这才提出经济学大思路调整的问题。
大的思路是,第一,创新出基于制度的技术经济学,或内生技术的制度经济学,实现二者的综合,以说明经济变化的技术来由,比如云计算如何产生了SaaS模式;第二,在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在垄断竞争基础上实现综合,以解释分享经济内生差异化为什么还能达到全局均衡,从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三,在古典经济学传统内部,实现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解决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在一般均衡理论中缺乏显示度的问题,使分享经济中的分成规律得以用可计量的方式显现。
这一大思路的出发点是,由于当前的分享经济对理论经济学的突破,主要是突破了隐含的生产力假定(原有理论未明言地预设 了工业化技术与工业化生产力),为了更替生产力上的前提假设条件,因此有必要注入技术经济学分析的新鲜血液;同时,由于分享经济涉及的利益问题,集中暴露出以往利益相互作用理论解释框架不统一,为了对利益分配给出“统一场”式的解释,在新的综合中,利益、分配、交易费用、制度、创新、垄断等诸多分散概念,统统被统一在代表复杂性的异质性这一概念中,用租值计量,简化博弈论为双层规划数学方法,对利益相互作用理论进行数学化处理。
了工业化技术与工业化生产力),为了更替生产力上的前提假设条件,因此有必要注入技术经济学分析的新鲜血液;同时,由于分享经济涉及的利益问题,集中暴露出以往利益相互作用理论解释框架不统一,为了对利益分配给出“统一场”式的解释,在新的综合中,利益、分配、交易费用、制度、创新、垄断等诸多分散概念,统统被统一在代表复杂性的异质性这一概念中,用租值计量,简化博弈论为双层规划数学方法,对利益相互作用理论进行数学化处理。
1.1.3 对利益分析方法的两大改进
分享经济理论通过新垄断竞争理论,将分享背后的利益相互作用机理,建立在技术经济关系——即生产力(技术关系)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结合——这种生产方式分析的基础之上。它带来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改进。
首先为政治经济学注入技术经济学的新基因。
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其起步期,是具有技术经济学基因的。突出反映在对英国纺织业生产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相当于现在互联网一样的技术革命)的深刻理解上。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的许多基本结论,都与工业技术、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这些结论有许多是不能脱离工业化背景而独立存在的。可以说,工业技术和工业生产力是内生在政治经济学中的。
但这一优良学术传统,在当代中断了。当信息生产力正在成为经济现代化新的驱动力和先导力量时,政治经济学家没有及时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传统,调整关于生产关系的研究结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信息技术作用的理解过于肤浅,对由此带来的分享这种生产关系改变不闻不问、完全失语。既然政治经济学不能自我完成与信息化趋势保持一致的工作,作为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专业研究者,就需要从外部引入技术经济学的传统,帮助政治经济学家更好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并沿着这一逻辑更新出符合互联网时代的新的生产关系结论,特别是关于“使用而非拥有”的生产关系结论,其中可解释的当前已大量发生且深具未来潜力的现象,就是劳动者在市场经济完全竞争中就可以获得高于资本家比例的剩余价值这一奇异现象。
信息技术革命背后代表的是一种差异化的异质性力量(又称创新),这是一种与同质化的生产力(工业生产力)相反的生产力。政治经济学已许久没有对生产力变革做出基础理论级(范式级)的反应。为推动它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正视信息生产力的存在,我们不惜引入技术经济学来“帮助”它“提高认识”,克服它隐含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工业生产力万古永存,因此生产关系(包括反映这种关系的排斥分享的排他性使用与专有范式)亦不变——的惰性假设;将工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推进到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其次是要为政治经济学注入均衡理论的新基因。
分享经济是一种表现为“平台分享+差异化增值”的新垄断竞争均衡现象。垄断竞争在张伯伦的原始出处里,代表着异质的完全竞争 。差异化在分享经济中通过分享主体APP的个性化、定制化实践,成为核心现象。差异化是垄断竞争与传统完全竞争的不同所在,它是产品从趋同(如传统中国制造)转向不同(如未来中国创造)的驱动力所在,也是分享经济背后的“技术-经济”发动机中的经济驱动力所在。
。差异化在分享经济中通过分享主体APP的个性化、定制化实践,成为核心现象。差异化是垄断竞争与传统完全竞争的不同所在,它是产品从趋同(如传统中国制造)转向不同(如未来中国创造)的驱动力所在,也是分享经济背后的“技术-经济”发动机中的经济驱动力所在。
政治经济学长期隐含着完全竞争假定,但这种完全竞争与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又完全不同。究其实质,差别在异质性范式——我们用异质性指代实证上的差异性(如个性化)——之上。政治经济学隐含着对人的理解上的异质性范式,这种异质性表现为对利益相互作用(社会关系)分析的坚持。为有别于新古典主义人性假定,把人的利益本身(人性)假定为异质性,以区别于物化(同质化)的人性假定。坚持以人为本,即坚持以社会关系的人为本,而不是以物化的人为本。这样就可以把政治经济学合理地解释为异质的完全竞争理论,或内生利益相互作用的完全竞争理论。如此,可以通过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进行同质-异质两种完全竞争理论在均衡水平上的比较。在找出分歧的实质以及融合的桥梁基础上,发现分享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对于这两个方面,我们分别用1.2节和1.3节来讨论,最后形成1.4节中综合的结论,说明为什么我们要用垄断竞争,而不是其他方法对分享经济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