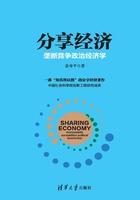
序言
面向信息大海,迎接春暖花开
很少为人作序。一是生性“喜新厌旧”,不愿为老生常谈的著述锦上添花;二是深信测不准原理,不愿用自己尚在跳跃的火花去干扰作者的深思熟虑。这次姜奇平先生邀我为他的新作《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写序,我没有犹豫,欣然接受下来。倒不是因为殊途同道的多年友谊,主要是欣赏他的思想火花和人文情怀,更因为我们还有个不约而同的使命,就是“揭示新经济规律,推进普惠信息社会”。
五年前,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核心组承担了一个研究项目“国家信息生产力发展战略研究”,姜奇平先生也是项目组成员之一。该课题报告认为信息技术的普及已经从信息交流、信息媒体,发展到以大数据、物联网、云服务、3D打印为标志的信息生产力阶段;并重新定义了信息生产力的概念,认为信息生产力就是“由信息或知识劳动者,以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为劳动工具,以信息资源为主要劳动对象组成的社会化协同生产能力”。信息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对传统生产关系、经济理论和社会制度造成新的冲击。但是估计不足的是,信息生产力及其新经济模式首先遇到了既得利益和传统经济理论的强烈抵制。
经过与学界、商界、政界多次对话、调研、讨论,同人学者又发表了系列研究报告、出版了多部专著,初步形成了以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为核心的中国新经济学术圈。在最近举办的信息社会50人论坛五周年纪念学术活动中,许多学者提出要从经济学的本源出发,用流行经济学的语境挖掘信息社会的新经济规律,建立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系统理论创新的通道。而这本《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就是用流行经济学语境挖掘新经济规律的一部厚重的学术文献。同时也是进一步将信息生产力纳入并改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次勇敢的尝试。
作者通过对信息生产力基础上的分享经济模式深入研究,提出了新垄断竞争理论,即“基础平台垄断+增值应用竞争”的双层经营模式;并且通过技术经济和数量经济分析,揭示出分享经济促进一次分配公平和实现普惠信息社会的重要机理。
本书还分析了传统的产权理论存在的缺陷,指出传统私有和公有理念根本涵盖不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分享经济。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如果实行信息私有制和信息垄断,互联网绝对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信息就是要充分共享,而且这种共享的特性提出了信息财富社会化内在的要求。”这使人想起了传统经济理论“公地悲剧”的著名典故,说的是产权不明晰,就会出现草原的过度放牧的不良后果。但是分享经济让人们把丰裕资源甚至冗余劳动时间贡献出来,放入“公共资源池”,以极低的费用实现效率与公平在更高经济形态上的统一。
回顾40年前,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极力主张公共资源私有化,并形成一场席卷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标志性贡献,就是将无线电频谱私有化。然而好景不长,近十年来的信息通信产业实践早已不支持公共资源的私有化,网络中立、平台中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就连由美国政府垄断的全球互联网域名分配与IP管理机构,也正式脱离政府和市场,成为非营利的社会化机构。
公共基础设施和信息财富的社会化,必然反噬传统的土地、机器等传统生产资料领域,其主要突破口就是淡化拥有权,强化使用权的分享经济。最近一位中国学者指出,中国的广义货币是130万亿元,但是真正流行的纸币才20万亿元。这110万亿元全是比特流,全是计算机网络里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按照传统思路去研究经济学,研究货币理论显然都已经过时了,所以随着技术的创新,经济理论也必须创新。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信息变成主要财富来源,又越来越体现社会财富以后,怎样激发创业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我记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作者丹尼尔•贝尔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到了信息社会,财富难以聚集,国家财政问题可能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信息时代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财富观,就是要用中产者的思维来重新找到联合投资创新的原动力,互联网支撑的众创、众筹、分享也许能开辟一条“泛社会化”的新路。
进入21世纪以来,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现在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贫富差距却拉大了,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绝对贫困。这个难题如何解决?当前存在三种思路,一种思路是让富人更富,再通过二次、三次分配救济穷人,这是国际上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的传统做法,但是副作用很大,效果证明并不可取。第二种思路是打土豪分田地,直接杀富济贫,这个来得快。或者干脆利用大数据搞精细计划经济,有人称为“信息时代的新计划经济”,我看都行不通。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舒尔茨是穷人经济学的创始人。他说过“贫穷的根源不是因为土地贫瘠和资源匮乏,而是由于长期的信息闭塞和教育落后”。但是办教育要百年树人,贫困地区的孩子被树起来也就飞走了。而通过互联网的外部效应,形成信息共享,就会快速提高穷人的视野和致富能力,这就形成了共同富裕的第三种思路。
有位专家曾经反驳我说,信息并没有那么大的功效,对于贫困地区来讲,最重要的是吃饭、喝水,然后是电、是路,最后才是信息。我说他前面讲的两个是对的,人不吃饭就死掉了,不喝水更受不了,可能还有空气比吃饭、喝水更重要。但这都是解决马斯洛需求模型的生存需求问题,而第二层需求就是信息。前不久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个《数字红利》调研报告,他们发现信息通信在偏远贫困地区,比道路、住房、厕所和清洁用水都重要!一个村庄可以没有路,可以没有电,但是需要信息。我国西藏自治区墨脱县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几十年不通电,不通路。要像唐僧取经那样披荆斩棘走上六七个小时才能到县城,而且要把袖子和裤腿拿绳子绑紧了,就这样身上还是爬进去许多旱蚂蟥,钻得人浑身是血。就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通信部门,靠人背肩扛把卫星通信、太阳能发电设备组装起来,开通了信息通信,让边民的信息视野一下子跨越了上百年。所以我多次讲信息化是促进社会均衡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最好切入点。
进到中国的寺庙主殿,会看到三尊佛像:西方往世佛、中方现世佛、东方未来佛。据说几千年前,菩萨问佛,修行的彼岸是什么?佛说从此地开始,经过十个恒河沙子那样多的世界(佛语一沙一世界),就到了一个叫作净琉璃的国度,这个国度每一个人上下左右都透明,也不会得病,没有贫穷和困苦,这就是修行的彼岸。当然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所限,世界不可能透明。现在我们用手机可以和千里之外的朋友互相视频发微信,主要是因为有了透明的玻璃纤维和大规模集成电路,而玻璃纤维和集成电路都是从沙子里面提炼出来的硅作为主要原料,现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离不开沙子和知识,它就是实现分享经济并使社会日益透明、人民普遍幸福的伟大基石。
250年前亚当•斯密提出一个悖论,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利己,然后就由上帝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去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叫作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利己之心能结出利他之果”。但是它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充分竞争,另一个是信息对称,这两个条件在现实中几乎找不到,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有人批评说帕累托最优具有奇迹般偶然性,实际上两极分化、经济失衡才是常态。
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喜欢讲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一对穷人情侣,女方很漂亮,有一头金发,但是连个发夹都买不起,小伙子只有一块怀表,但是买不起表链。要订婚的时候,女方把头发剃了换了钱,买了一个表链送给男友,小伙子卖了怀表买了个发夹给女孩,弄得不欢而散。由此来证明,每个人都利己才能更有效率。其实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现在有手机网络,年轻人经常微信聊天就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另一个故事是制度经济学派爱讲的和尚分粥的故事,说的是七个和尚轮流分粥,都先给自己多分,别人就有意见。后来定了一个制度,谁负责分粥,就只能取走最后一份,这样分得就平等了。然而现实市场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缺乏诚信的值班和尚完全可以事先作弊,让大家看起来貌似公平。我国有法律界人士就主张,下饭馆也要事先签订合同,里面写清有几块肉、几根菜,出了纠纷打官司好有证据。结果什么事都得诉诸法律,律师们发财了,老百姓更悲惨了。北京有人买了几斤羊肉怀疑里面掺了猫肉,告到法院,法院说谁主张谁取证,你到指定单位去化验,化验费需要7000元人民币。那么普通老百姓这个官司怎么打?靠法律约束只能是极少数的行为,老百姓把打官司当常态,这个社会还能运转得动吗?我们现在的法律条文已经很厚,但是最后还是出现了老人摔倒“扶不扶”、遇到病人“救不救”、看到不合理现象“管不管”的尴尬。因为法律要讲证据,你自己必须证明你自己是好人,甚至还要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制度万能论的悲哀。
所以我认为“利己之心根本结不出利他之果”,整个社会都坏了良心,制度也会成为保护坏人的帮凶,而利他主义的说教同样掩盖不了背后的贪婪。现在许多前卫学者也开始批评经济利己主义,因为“一辆辆汽车聚在一起,利己主义决策肯定会带来一场噩梦”。所以我也讲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开车让行。有人在城市郊区一座小桥观察交通情况,桥很窄,一次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但是由于信息透明,每个司机都能看到对面的情况。总是这边过四五辆,就有一个司机主动停下来让那边过四五辆,大家都很自觉,等待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大家都看得清楚,我不让你过去,我自己也过不去。
另一个故事说,郊区农民在路边摆一个桌子卖菜,标好价钱,过路者买走就把钱放在一个盒子里,不需要有人看管,这说明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是希望公平交易。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个漏洞,出现少数恶人破坏规则怎么办?我们过去常说“人在做,天在看”,现在的“天”有些不灵了,有的人看见了也不愿意惹麻烦。所以我很赞成网络实名制,满世界都是电子眼,出了问题可以追溯。当然电子眼只能安在公共场所,放在人家家里就侵犯隐私权了。现在可以称作“人在做,网在看”,这样就能够快速形成平等交易,比较圆满地解决多元重复博弈模型的迟滞问题。
150年前,法国老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巴斯夏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想牺牲别人让自己活着”,结果是谁都活不好。他还说“未来产权流动的主要方向不是从公共部门流向私人领域,而是由私人领域流向公共领域”。可悲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伪善或诡异文化糟粕,与经济利己主义一结合,造成了太多的“公地悲剧”。但是这种“法术”在网络时代越来越不灵了,马云说,随着信息日益透明“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我把它称作公共关联理性。
互联网新玩法就是“必须为别人创造价值,你才能获得自身利益”。默克制药集团老板说,“药品旨在救人,不在求利,这一点记得越牢,我们的利润就会越大”。本书作者姜奇平先生也有一句名言:“要让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发财。”我认为分享经济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激励机制,进入“只让好人赚钱的时代”。
有人担心互联网平台发展,会不会导致贫富差距更快地拉大?就像阿里巴巴、苹果这样的大公司,富可敌国,与普通小微企业的收益形成巨大反差,从而造成分配的更大不公平。而《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一书可以告诉大家:“这种观点首先不符合事实,苹果商店模式中的三七分成,使普遍劳动者获得了收入的大头(70%),而苹果公司只得到小头(30%)。只是劳动者分散,而平台集中,让人们误以为利润都被平台公司获得了。事实上,苹果公司一家独大,只是说明资本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使原来众多的(分成比例更高)资本拥有者,集中为了极少的(分成比例更低)资本拥有者。这样发展下去,资本拥有者在整体上占有的份额是在萎缩之中,而不是扩大之中。”
社会不能没有人文情怀,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曾惊呼:“现代经济学在快速发展中迷失了救世的激情与公平的梦想!”我想演绎一个著名的《圣经》故事来结束是序:某使者死后,上帝带他去了地狱,看到许多人都拿一把长把勺子,围着一桌好吃的饭菜疯抢,搞得遍地狼藉,就是吃不到自己的嘴里去。然后他又回到人间,看到几位强者拿着长把勺子轮流给大家喂饭,人们还是感到不公,争得不可开交。最后上帝带他到了天堂,这里每个人都拿着长把勺子互相喂饭。
如果说,耕牛生产力时代人们只能靠自己吃饭,机器生产力时代人们要靠少数掌握权力或者资本的人吃饭,那么信息生产力时代人们必须学会互相喂饭,而互联网分享经济就是人们相互喂饭的长勺。读者如果相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哲学原理的话,那么我就借用该书的结语:让我们共同“面向分享经济汪洋大海,迎接未来社会春暖花开!”以是为序。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