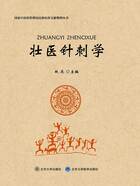
第一节 概述
壮医学是中国传统医药学领域中一个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地域性民族医药学分支;壮医针刺学是壮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90%以上的壮族人口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及其先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的医药体系,壮语称为“依托”[jw1to3]。“依”[jw1]即医药,“托”[to3]即“本地”“土著”之意,译为土医、土药。壮医所使用的药物均取自自然,而其特色的医疗方法尤以针疗著称,也是一种很有地方特色的自然疗法。壮医药萌芽于原始社会时期,至今已发展成为壮药内服、外治方法优势明显的包括壮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药刮和角疗、灸法、挑针、毫针、陶针、星状针以及其他金属针等数十种内外治疗方法,并以其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浓厚的地方特色长期流传于民间,在我国民族传统医药中更是独树一帜。现有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实地调查资料,特别是广西武鸣马头乡西周古墓出土的青铜针和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壮族先民的医用针具以及诸多壮族特产药物都证实了壮医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而针刺疗法也是客观存在的。壮医针刺疗法至少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壮医针刺理论的形成,来源于壮族人民对生活经验、生产经验和医疗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族文化的养分,形成了自己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考古业已证实,早在数千年到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就已有壮医药的萌芽。在广西出土的许多石器时代的文物里,就有壮医药伴随壮族人生活实践而产生的实物例证。如桂林甑皮岩出土的一些早期的石器工具、武鸣县马头乡西周古墓出土的青铜针、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银针等,都是对壮医药悠久历史的见证。但是,在壮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壮医虽然长期活跃于壮族民间,但始终没能形成自己的系统完整的医疗理论体系,壮医针刺疗法也是如此。其主要原因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壮族都没能形成本民族规范统一的通行文字。也就是说,壮族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没有语言的载体——文字,更谈不上规范统一的通行文字了。
虽然历史上壮族没有形成本民族规范统一的通行文字,但是壮族人民的发明创造,如文学艺术、科技、医药的史迹等,客观上又需要有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便能代代相传。于是,随着壮汉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到了唐代,壮族一些地方的统治者,开始借助汉字及其一些偏旁部首,创造了一种“土俗字”,即古壮字。据考证,在古壮字的兴盛时期,壮人用土俗字来记账,写家谱、族谱、药方是很普遍的。因此,壮族先民的医药经验,有一部分有可能通过古壮字的记录而保存下来。不过,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壮医的用药经验、诊断方法、医疗技法等,主要还是靠师徒授受、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至今;而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尤其是理论部分,则散见于历代汉文史籍,尤其是广西各地的地方史志或中医医典著作中。长期以来,壮医药最缺乏的就是文字这一载体的总结、归纳、凝练和理论升华,故在历史上,未见有一本完整的壮医药典籍形成并流传下来。以至今天我们要考究壮医针刺学发展的历史,只能从一部分不完整的汉文史料的记载以及民间传说中去窥探其一斑,从一些零散的记述中去推究壮医针刺的历史原貌,从一些中医医史文献中大致了解其历史发展线索。
尽管可获得的直接史料不多,但我们通过对一些有关壮医药的考古资料与记述,以及在壮族民间的实地调查,还是可以对历代壮医对针刺治疗疾病的认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从已发掘出的文物古迹来看,在广西宁明县境内,著名的壁画群——花山崖壁画就坐落在明江河边的悬崖上。考古工作业已证明,花山崖壁画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壮族先民的艺术杰作,不仅在国内岩画艺术中可谓首屈一指,就是在世界岩画艺术中也堪称一绝。花山崖壁画是研究古代壮族社会生活的极有价值的史料。花山崖壁画蕴含的社会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壮医学(含壮医针刺)的内容。从花山崖壁画的画像来看,壮族先民至少在当时对人体的解剖结构有了一定的认识,并懂得通过舞蹈、气功等运动来祛病健身。有专家考证,花山崖壁画有可能是诊疗图,其中有施术者,有持器者,有受术者。从画面来看,花山崖壁画呈现的场景有可能是壮医针灸治病的治疗图,或至少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有关壮医药的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中医药典籍《黄帝内经》。中医药是我国各民族医药的总汇,而《黄帝内经》则是最具代表的医典之一。在《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载有:“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盛处也,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跗,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这里的南方应当包括壮族地区在内。《黄帝内经·灵枢·经脉》云:“肝足厥阴之脉……上循足跗上廉。”《医宗金鉴》云:“跗者,足背也。”
迄今为止,在我国南方,只有在壮族聚居的广西武鸣县及贵港市有金属医针实物出土,其中马头乡青铜针为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金属医针;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银针为汉代的金属针具,与《黄帝内经》的成书处于同一年代。故有专家认为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西周古墓出土的青铜浅刺针和在广西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银针为《黄帝内经》“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论断提供了实物例证。马头乡青铜针、贵港市银针也是壮族先民用针刺治疗疾病的工具。例如,对一些热病、中毒等,壮族先民即用放血疗法治疗。同时也说明了,壮民族应是最早使用金属医针的民族。
广西德保县已故的著名老壮医罗家安在其所著的《痧症针方图解》一书中,就明确以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盛阳盛对各种痧症进行分类,并作为临床辨治的参考。《痧症针方图解》为壮医针刺较为完整的一部民间手抄本,有关人员正在对该手抄本进行发掘整理。
历代广西地方史志中,都有关于壮医针刺治疗疾病甚至是一些急危重症的记载。例如,民国时期广西《宁明州志》《恭城县志》记载了壮族先民运用针刺放血抢救中暑、昏迷等急症。《宁明州志》载:“五六七月盛暑伏阴在内,乡村人又喜食冷粥,故肩挑劳苦之人,多于中途中暍而毙,俗谓之斑麻,又谓之发痧,以手擦病者自(白)臑及臂,使其毒血下注,旋以绳缚定,刺其十指出紫血,甚则刺胸刺腮刺舌,多有愈者。”《恭城县志》载:“役劳苦之人,一或不慎,辄生外感,轻则身骨疼痛,用刮摩之法,重则昏迷不知,非用瓷瓦针将十指刺出紫血,则命在旦夕,宜急不宜缓,急则生,缓则死,生死相关,不可忽也。”
近年来,广西在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中,收集到不少壮医药民间手抄本,其内容绝大部分皆以针刺疾病为主,典型的有《痧症针方图解》《童人仔灸疗图》《此风三十六种》等。这些手抄本尽管没有公开出版,但其在民间流传,对保存和普及壮医药知识,促进壮医针刺诊疗水平的提高,提高壮族人民的健康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