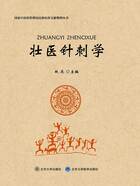
第二节 壮医针刺的起源
壮族人民在长期同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医学,是壮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壮族医学宝库中,壮医针刺法以其用具简单、操作简便、疗效显著而世代流传,经久不衰。
壮族先民对针刺治疗疾病的认识,是与壮民族的医药起源同步的,或略早于医药。医药起源于原始的实践经验,壮族人民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斗争中,通过反复的实践,并经过理性思维后,对某一种疾病,或某一种疗法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就会有意识地运用某一种方法来解除某种病痛。这种有意识地运用某一种方法来解除某一种病痛的行为,则早已超越动物本能,应视为最早的壮医治病经验。这种最早的治病经验,就是壮医针刺治病理论的基础。
正如上面所说,《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就明确提出了“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明确地指出了九针的产生,即针刺疗法的发祥地,特别是微针疗法的起源地应是祖国的南方。诚然,《黄帝内经》所说的南方不一定就是特指广西壮族地区,但通过地理位置及历史文献的综合考究,这个“南方”应当包括广西壮族地区在内。先秦时期,我国长江以南是越族人聚居地,史有定论。壮族来源于我国古代的越人,世居粤、桂、滇、黔,居地属于中国南方的一部分。《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命禹“南抚交趾”,说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的年代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堪称古代的岭南植物志,书中所载大量地名即在广西境内。这些都可以佐证,壮医针刺疗法起源于原始时期南方壮族聚居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较盛行,随着汉壮文化交流而传播到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由此可见,“九针”最早起源于南方,并由南向北传播,这与壮族先民的发明创造密不可分。
一、出土文物见证壮医针刺疗法的起源
壮族是广西的土著居民。先秦古籍所载之南方疆域包括广西地区在内。《医部全录》卷七说:“南方之气,浮长于外,故宜微针以刺其皮……微针者,其锋微细,浅刺之针也。”但微针形具如何,久已失传。
1985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工作者在壮族聚居地大明山脉周边的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古墓群,该古墓群的年代系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在标为101号的墓穴中,出土了2枚精致的青铜针。这2枚青铜针在出土时,表面仍有光泽感,但其中1枚在出土时已残断。考古学家认为,从这2枚针的外表可以看出,针的铜质好、硬度高,针具的制作工艺精细、表面光滑、边缘整齐。针体通长2.7厘米,分针柄、针身两部分。针柄扁而薄,呈长方形,长2.2厘米、宽0.6厘米、厚0.1厘米。在针柄的一端有长仅0.5厘米,呈圆锥状的针身,其直径仅0.1厘米,针锋锐利。针身看上去像柚子树上的刺,估计是古人模仿天然植物刺铸造而成的。从青铜针的外形观察,作为浅刺医疗工具的可能性极大。因方形的针柄与短小锥形的针身差异较大,后无针孔、前无针钩,不能作拉曳穿透缝纫布料或兽皮之用。又因其针身过小,针柄造型不利旋转,不可能作为钻磨装饰品的成形工具。而方形的针柄,极适于术者稳持针具,短小锐利的针身,正是为了达到浅刺皮肤,又不重伤肌肉的目的。经过专家论证,壮族先民将该针作为医用浅刺针具使用,这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金属医针,如图1-1所示。

图1-1 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出土的西周时期的2枚青铜针
广西土著居民(包括秦以前的骆越人)有将死者生前常用之物随葬的习俗,由此推测,墓主人生前很可能就是当地的行医者。据史料记载,中原文化大量传入岭南是从秦以后才开始的;而在秦以前,广西主要是骆越人的势力范围,与中原联系较少。战国时期,楚国势力逐渐南移,但楚的势力范围也仅限于桂北、桂东一带。秦统一岭南后,由于大明山脉的阻隔,交通不便,武鸣地区直至清代仍然任用本民族的首领为土司,实行与汉族地区政治、经济制度不同的土司统治。武鸣一带在秦以前属骆越人的领地,历代文献多有记载,如《旧唐书·地理志》载:“……水在县北,本徉柯河,俗呼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曰温水,古骆越地也。”经民族学家考证,骆越人是如今壮族人的祖先。在民族融合、分化、形成的过程中,大部分的古骆越人、西瓯人后裔成为今日壮族。如今武鸣县马头乡附近的乡名,如板欧、板陶、绿洪、都炉、吉麻等仍保留着古越语称谓。这些称谓唯有用壮语才能解释,这就从语言学证实了古骆越人与现代壮族在起源上有继承关系。在这批墓葬群中,出土了一种铸造模型石范,这表明在广西地区,已能自制青铜器。若将马头青铜针与以往各地出土的砭石及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青铜砭针相比较,则会发现它们的造型及风格大不相同。这些都说明了马头青铜针是壮族先民——骆越人在冶炼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自己制造的。该针的使用族体当然也是土著民族——壮族先民。马头青铜针是广西古代骆越人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完全是当时人们和疾病做斗争的需要,是先民长期运用针刺疗法的产物。
而在此之前的1976年7月,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3枚银针,其外部造型相似,针柄均为绞索状,针身均为直径0.2厘米的圆锥状,锋锐利,3枚根针的针柄顶端均有一圆形小孔,长分别为9.3厘米、9.0厘米、8.6厘米(如图1-2所示)。从外形观察,3枚银针的造型与现代针灸用针极为相似,可以确认为医疗用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绞索状针柄的金属制针具。这种针柄对后世针具的针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一直沿用至今,在我国针具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图1-2 1976年7月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3枚银针
壮族先民创制金属针具并不是承自他族,而有着自己的渊源。在几乎遍及广西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制作精巧的适于刺割的治疗工具。
石凿(凿状砭石)在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早期遗址出土。石灰石磨制而成,很薄。长9.8厘米、宽1.6厘米、厚0.4厘米,下端有锋利之刃缘。
骨锥在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早期遗址出土,由动物长骨磨制而成。一端磨光磨尖,另一端保持扁平形的原形锥顶,锥长8.2厘米,径最粗处0.4厘来,针锋锐利。
笄状骨针在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早期遗址出土。由动物长骨磨制而成,全长8.2厘米,径最粗处0.6厘米,器身扁圆,两端尖锐锋利。
鳖甲刀在广西横县西冿水库新石器早期遗址出土,器身近似梯形,全高5.7厘米、刃宽5.3厘米,用鳖甲片磨制而成。周边光滑,底边呈单面刃,刃部极薄锋利,一面较平滑,另一面中间左下角有一交叉十字痕,中间凹,两边缘凸,如图1-3所示。

图1-3 1966年在广西横县西冿遗址出土于的鳖甲刀
三棱石针(砭针)在全州县卢家桥新石器中期遗址出土。黑燧石磨制而成。通长7.5厘米、直径1厘米,通体光滑,中身部分圆身为柄。使用部分在两端,一端呈三棱形,锐利、形若锋针,供浅刺用;另一端呈圆柱形,略小于中身柄部,供按摩用,有中身为柄、两端为用之特点。
广西气候炎热,荆棘丛生,皮肉破损后,极易感染化脓。以上所列广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刀针形体小巧,锋部锐利,适于刺血排脓,广西的原始人类曾将之广泛使用,作为常备之物。
二、地理环境影响壮医针刺疗法的起源
医学的产生,与人类长期同自然环境做斗争的历史分不开。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生活习惯。这种外界条件影响人的体质,导致了疾病和治疗方法的地域性。如《黄帝内经》所载,治法之异,是由“地势使然也”。广西地处五岭之南,其气候特点,《岭南卫生方·原序》总结为“岭南外号炎方,又濒海,气常燠而地多湿,与中州异”。广西属亚热带低纬区,长年受太阳强热辐射,又濒海,故气温高、雨水多、湿度大,加之广西土著居民自古有嗜酸食胕的习俗,而且渔猎活动是主要的谋生手段,故发病多与湿遏热伏有关,多患以全身肌痛为主要症状的“痹”病。对于南方这类地方病“痹证”,使用微针往往能获得较好的效果。正如唐代王冰所说:“酸味收敛……湿气内满,热气内薄,故筋挛脉痹。微,细小也。细小之针,调脉衰盛也,故九针南人甚崇之。”
“瘴”这一古病名在广西有关历史古籍中很常见,是壮医针刺的一大类疾病。据《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土多瘴气。”马援南征时,“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说明岭南包括壮族地区瘴气为害之烈。瘴的成因,自古论者不一。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壮族先民对瘴气的治疗方法及对瘴气病因病机的认识。《岭外代答》载:“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瘴,两广唯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也。”《桂海虞衡志》曰:“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嘉靖《广西通志》认为与水泛酷暑有关,“故春更多雨,江常泛涨,六七月之交,炎暑酷甚,积雨蒸郁,瘴气间作”。清人赵翼《檐曝杂记》认为与广西森林茂密有关。该书引靖西县父老的话说:“昔时城外满山皆树,故浓烟阴雾,凝聚不散,今人烟日多,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气尽散。”总之,广西炎热多雨,利于动植物大量繁殖生长,古代人烟稀少,山多林密,落叶死兽腐败后,利于病菌生长繁殖。若经雨水冲入溪涧,污染水源,特别是在洪水泛滥之后,极易引起瘴疫流行。瘴疫对生命构成了巨大威胁,壮族先民能在瘴疫之地生存下来,发展成为今日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针刺疗法对民族保健起了重要的作用。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提到:“夫岭南青草黄芒瘴,犹如岭北伤寒也……今得瘴毒……瘴气在皮肤之间,故病者有头痛、恶寒、腰背强直,若寒气在表,发汗及针,必愈。”《岭外代答》有“南人热瘴发一二日,以针刺其上下唇,其法卷唇之里,刺其正中,以手捻去唇血,又以楮叶擦舌,又令病人并足而立,刺两足后腕横纹中青脉,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应手而愈”的记载。《古今医统大全》载:“若夫热瘴乃是盛夏初秋……其热昼夜不止,稍迟二三日不治,则血凝而不可救矣,南方谓之中箭,亦谓之中草子。然桃草子之法乃以针刺头额及上下唇,仍以楮叶擦舌,皆令出血,徐以草药解其内热,应手而愈,安得谓之久而死耶?”古籍认为瘴与痧同为一病,如《赤雅》曰:“又中瘴失语,俗呼为中草子。”《痧症全书》认为:“江浙则为痧,闽广则为瘴气。”若痧瘴同为一病,那么治法则相同。对于常见痧症,挑刮是常用之法,如《痧胀玉衡》提出刮、放(浅刺)、药,是疗痧(瘴)三大法,并谓“血肉痧,看青紫筋刺之,则痧毒有所泄”。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比见岭南人初有此者(指初患卒中、沙虱毒之症),即以茅叶刮去,及小伤皮则为佳……已深者,针挑取虫子……若挑得便就上灸三四壮,则虫死病除。”这是岭南人挑治卒中、沙虱毒的方法。目前,此法仍在广西地区广为使用。
这种情况说明,广西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产生特殊的疾病,而针刺疗法对广西病种有特殊的疗效,是针刺疗法产生于广西地区的主要原因。针刺疗法在广西壮族历史上出现之后,随着治疗的迫切需要及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和提高,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针具的改革与变迁及针刺经验的增加与积累两方面。
瓷针是目前壮医常用的针具。《本草纲目》认为,“今人又以瓷针刺病,亦砭之遗意也。”瓷针既为砭之遗意,那么它的发展线索则是由旧石器时代的石片、石刀,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砭石;随着瓷器的出现,瓷针也代替了砭石。考古资料证明,西汉晚期,广西已出现青瓷器,并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由此推测,壮族先民使用瓷针至少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西周末年使用的青铜浅刺针,针身短小,外形酷似柚子刺。广西植物刺的大量丛生,为古人类的浅刺实践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经过石器时代漫长的实践过程,壮族先民积累了丰富的针刺经验,金属缝衣针出现后,鉴于其具备微针的特点,加之取材方便,同时基于广西地区对针具的急切需要,很快就被引入针刺领域,并广泛传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