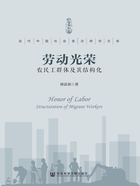
农民工的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工群体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但是学界对“农民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而且,随着农民工现象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随着农民工成为一个屡见不鲜的研究话题,“农民工”这个词语已经成为一个常识性词语,关于农民工的很多研究也就跳过“概念界定”环节而直奔主题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农民工的界定问题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关于农民工性质的想当然的本体论假设是经验研究的最根本内容,因为这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问题的提出和理论的选择(Bourdieu et al.,1991;Archer,1995)。
事实上,学术界对于农民工的界定并不统一。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界定方式。首先是产业界定。比如,吴海峰(2009)认为,在从传统农业色彩浓重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会逐步脱离乡村土地,转变为准产业工人(农民工),并进而转变为正式产业工人。何美金和郑英隆(2007)也认为,农民工是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劳动者形态。其次是身份界定。沈立人(2005)认为农民工是兼有两种身份和双重角色的人群。注重农民工身份的界定方式更多地强调农民工具有农业户口,但是他们从事非农业活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刘传江,2004;Cai and Chan,2009)。最后是行为界定。围绕其行为特征,关注其打工生活,农民工往往被称为“打工者”(工友之家,2013;王颖,2005)。但是,具有价值诉求的研究者往往从价值的层面上区别“农民工”、“打工者”和“新工人”等词语的社会影响,而没有将“打工”作为其行为特征来对农民工进行客观界定(比如,吕途,2012;汪勇,2007)。
由于大量的第二代农民工几乎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中国工运研究所,201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2009),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农民工的身份界定超越了户口所界定的范围(Zhan,2011;黄锟,2011),所以产业界定和身份界定已经不足以全面描述农民工的生活状态了。为了更好地描述我国农民工的共同特征,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以其行为特征为基础,并综合身份界定和产业界定的元素而进行界定。如此,农民工可以被界定为以其特有的“打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劳动者群体;所谓打工就是离开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权的农村村落,在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来到城镇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并以劳动换取工资以满足生活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打工生活方式产生了农民工不良的(甚至是恶劣的)生活状态。他们要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尤其是传统节假日和农忙期间(Wang,2005),需要回农村与家庭团聚或从事短暂的农业活动;在城市中,他们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需要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长时间工作,但是他们的平均工资低于城市居民(Wang et al.,2002;Hannan,2008);他们的工作既不安全,也不稳定,甚至要频繁地变换工作(Chan,2010b);虽然他们的工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很少有完全的劳动合同(Lee,2007;Meng and Chris,2010),没有完全享有包括医疗保险、就业保险、工伤保险、退休金等在内的福利待遇和社会服务(Zhan,2011;Meng and Manning,2010);他们居住在狭小的宿舍或民房中,而且很多人必须和其他家庭成员分离(吕途,2013)。此外,他们恶劣的生活状态还带来了诸多心理问题,比如精神衰弱(Mou et al.,2011;Qiu et al.,2011)。总而言之,农民工构成了我国社会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尤其是没有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Solinger,1999;Fan,2002;Lee and Meng,2010;Taylor,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