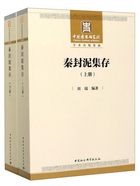
序
刘瑞研究员最近嘱我为其新作《秦封泥集存》撰序,他发给我的电子版书稿有上千页,可谓洋洋大观的巨著。看到《秦封泥集存》稿之后,使我首先想到的是刘瑞为什么以此为题从事研究?
二十多年前,刘瑞早在学生时代就投入了“秦封泥”的整理与研究,那时他曾经协助周晓陆、路东之先生编著《秦封泥集》,2000年5月三秦出版社出版此书,当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秦封泥也成了刘瑞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起跑线”,时隔20年后,现在刘瑞又整理、出版《秦封泥集存》,这是多么有意义的“时间巧合”与“学术接力与跨越”。
刘瑞研究员能够出版《秦封泥集存》这样的皇皇巨著,与他的学术经历密不可分。他在大学与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曾经先后在中国考古学、秦汉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与历史地理学的“重镇”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博物馆学家周天游先生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等各位老师,接受考古学、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与历史地理学全面、正规的学习与训练。刘瑞从大学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后,二十多年来又先后参加了南越国宫城遗址、秦阿房宫与秦汉上林苑遗址、秦咸阳城与汉长安城之间的渭河桥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等多项秦汉考古的重大项目,上述考古项目均属于秦汉历史的“社会大传统文化”,或谓之“国家文化”。他是国内目前在秦汉考古学领域参加、主持重大秦汉田野考古发掘项目最多的学者之一,更是国内十分少见的集考古学、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与历史地理学于一身的学者。这样的学术背景为他从事秦汉封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秦封泥集存》是刘瑞研究员关于秦封泥研究的大作。根据《辞海》关于“铭刻学”的定义,它属于“考古学分支”学科,而铭刻学包括内容有“商周金文(铜器),战国秦汉以来印章、简牍、封泥、石刻和陶器上的文字等。”(《辞海》1999年缩印本第1490页)把“铭刻学”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是夏鼐、王仲殊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提出的。他们认为,“铭刻学”“对原史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之“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8页)从以上《辞海》关于“铭刻学”定义,封泥属于“铭刻学”。
我认为铭刻学之于历史考古学的重要性,在甲骨学、简牍学、封泥学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而在甲骨学、简牍学与封泥学中,封泥又因其印文主要内容多为与国家行政机关与地方政权有关的“官制”与“历史地理”方面的文字内容,致使其所承载的历史权重自然不是其它“遗物”所可比的。
在中国古代封泥集中使用的一千多年间,秦汉时代的封泥又可谓封泥之制的盛期,一方面从现存中国古代封泥来看,主要是秦汉时期的封泥遗物;另一方面,秦汉封泥文字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官制与国家空间的行政区域的“政治文化”,而秦汉时代是开创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时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时代,其政治文化上承夏商周三代,下启秦汉帝国以后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作为反映秦汉帝国这一“政治文化”物化载体的秦汉封泥,其重要学术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封泥的这一重要社会“功能”,是由于“在春秋战国以后长达千余年时间里,官私印章的使用及其征信、标记功能主要是借助封泥这一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可以说,玺印的使用与封泥不可分离,以印封泥,也即是玺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实用意义。”作为权力标识的玺印,无疑是“国家文化”的重要“信物”。封泥的上述功能,使“封泥文字对古代文献记载的官制、地理资料的订正和补充是封泥的主要价值所在。”(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中国古代封泥的著录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金石学家吴荣光《筠清馆金石》一书最早,从清代晚期到民国时期的封泥著录作者主要是金石学家、收藏家。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中国各地发现的封泥数量约3000枚。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的封泥发现倍增,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封泥的发现之多,与以前一个半世纪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大部头封泥图书,如1994年上海书店出版的孙慰祖主编《古封泥集成》、2000年周晓陆、路东之主编《秦封泥集》、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慰祖主编《中国古代封泥》、2010年西泠印社出版的杨广泰编著《新出封泥汇编》、2018年西泠印社出版的任红雨编著《中国封泥大系》和这部刘瑞即将出版的《秦封泥集存》等等。
上述封泥图书可以分为两类:“通史类”与“断代类”封泥著作,前者有《古封泥集成》、《中国古代封泥》和《中国封泥大系》,后者有《秦封泥集》、《新出封泥汇编》和《秦封泥集存》。一般来说,“通史类”封泥“集成”的封泥种类与数量,要比“断代类”封泥“集成”的种类与数量要多。“通史类”的《古封泥集成》、《中国古代封泥》、《中国封泥大系》分别收录不同朝代封泥2642枚、8700枚、15777枚,“断代类”的《秦封泥集》、《新出封泥汇编》、《秦封泥集存》分别收录封泥1165枚、7800枚与9218枚。我们就上述著作的封泥收录数量进行比较可知,《古封泥集成》、《中国古代封泥》、《新出封泥汇编》与《秦封泥集》其各自收录秦封泥的数量均少于《秦封泥集存》。《中国封泥大系》收录历代封泥15777枚,但是其中“秦封泥”只有5486枚,而《秦封泥集存》收录秦封泥多达9218枚。至于《秦封泥集》与《秦封泥集存》收录秦封泥的数量更是相差悬殊,前者仅是后者封泥收录数量的12.64%。而从封泥的种类来看,《新出封泥汇编》收录秦汉封泥7800枚,有1272种,《秦封泥集存》收录秦封泥9218枚,有2350种之多。由此可以看出,《秦封泥集存》整理、收录的封泥资料之丰富、种类之众多,都是十分突出的,自然其对秦封泥、中国古代封泥与秦汉考古学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研究具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秦封泥集存》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在本书的框架设计上的学术性与科学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只要对其目录与其它同类著作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作者虽然是进行的秦封泥汇编、集存,但是他把这一工作置于“社会史”之下,突出了封泥的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性,其重要表现是《秦封泥集存》的目录设计。作者参照《汉书》之《百官公卿表》与《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来安排封泥编目,从“百官”(“国家政权”)到“地理”(“国家空间”),从“中央”到“地方”,从而使读者可通过《秦封泥集存》“进入”两千多年前的秦王国与秦帝国的方方面面。
在《秦封泥集存》的付梓之际,我写了上面一些文字,就是希望今后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著作面世。
刘庆柱
2020年3月12日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