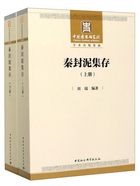
前言
玺印,是古人用作信用凭证的器物,“印章的主要作用在与凭信之证据,表示某种集团的、阶层的、官方的、私人的、公用的、商用的、艺术的等等有关时效、地域、权威、身份、价值、意见的凭信”[1],因此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印,执政所执信也。”文献中,印亦称玺。东汉刘熙《释名》曰:“玺,徒也。封物使可转徒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2]秦汉时期玺印的地位和变化,在东汉蔡邕所著《独断》中有较详细记载[3]:
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玺以玉,螭虎纽)[4]。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玺”;《春秋左氏传》曰:“鲁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此诸侯、大夫印称玺者也。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纽,唯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5][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6]。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
《独断》中所言的“固封玺”见《礼记·月令》,该句卢文绍在抱经堂丛书本的《独断》校中说:
臧在东云:《礼记·月令》“固封疆”,郑注:“今《月令》疆或为玺。”《吕氏春秋》、《淮南子》并作“固封玺”。《太平御览》682载应劭《汉官仪》引《月令》曰“固封玺”,此亦用今《月令》也。
《独断》所言的《春秋左氏传》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类似内容还见《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曰:“玺,印也,古者尊卑共之。《左传》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秦汉尊者以为信,群下乃避之”,与《独断》所言基本一致。
一 封泥的发现与确认
作为凭信的意义的玺印,要通过某种特定的载体才可体现。封泥就是玺印在泥上钤抑的产物,是玺印蕴含意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如周晓陆、路东之所言,“在论及南北朝——隋唐之前玺印用法时,恐怕最为重要的,即是在封泥上多体现的玺印的使用了”[7]。
战国秦汉时期,往往会在某些器物、文书等外置检、囊等,然后在系绳上置泥而在其上钤抑印章。睡虎地秦简《金布律》有“官府受钱者,千钱一垒,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的记载,就是秦时期印章使用后的规定。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也有“毁封,以它完封印印之,耐为隶臣妾”,是对非法打破封泥后用其它封泥冒充的惩罚。《二年律令·行书律》规定“书以县次传,及以邮行,而封毁,□县为劾印,更封二署其送徼曰:封毁,更以某县令若丞印封”,规定了文书在传送过程中,封在文书外的封泥,如果意外破裂后的补救措施。而在汉简中,也确实有不少“封破”“印破”的当时的相关记录保留下来[8]。
虽然有确切的的玺印钤抑于泥上形成封泥的记载,而且从后来发现的情况看,古人使用玺印在泥上钤抑的时间也很长,但在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并未发现有关封泥的任何实物记录。特别是从宋代金石学开始大兴之后,在日益昌盛的金石收藏中,虽然传世或出土铜器、碑刻等古代遗物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有宋一代富裕而有闲的士大夫家中,但不知何种原因,直到清代中晚期,封泥才第一次被发现,之后当然就如井喷般被收藏与研究,成为一个新的文物类别。
从文献记载看,封泥在被发现和进入收藏家手中并加以大规模著录的时间——与甲骨文几乎一样——我们对与之有关的人物、时间和地点都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据《筠清馆金石》等文献记述,见于记录的封泥的第一次出土是道光二年(1822年),“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之后“估人赉至京师,大半碎裂。诸城刘燕庭、仁和龚定庵各就估人得数枚,山西阎贴轩藏数枚,余不知落何处。”[9]。
封泥“再发现”后就这样进入了收藏家和研究者眼中。最早的封泥著录,目前一般都上溯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吴荣光南海吴氏家刻本《筠清馆金石》,之后陆续有咸丰二年(1852年)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及光绪三十年(1904年)刘鹗抱残守缺斋《铁云藏陶》[10]等等。不过随着童衍方对释六舟旧藏道光十七年(1837年)汉封泥拓本的研究,封泥著录出现的时间被提了五年[11]。
由于封泥是新新发现的一种器物,因此在封泥发现和著录的早期,它的名称并不固定。如释六舟藏汉封泥拓本“黄神越章”封泥下钱泳跋称其为“印笵”[12],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封泥著录《筠清馆金石》中,将6枚封泥在“汉印范”下进行罗列,后更称“此汉世印笵子也”[13],显示出当时的学者尚不能判断它们的实际用途。
此后的情况,如王献唐所言,“戴醇士知为搏土封题之用,名曰抑埴(见《习苦斋诗集》),仍非正称[14]。迨刘燕庭据《续汉书·百官志》始定为封泥(见《泥封印古录》胡序),其《长安获古编》录入西安所收封泥三十枚。而仁和胡琨合刘陈旧藏,编为《泥封印古录》,反疑刘说不信(见原书胡序)。赵益甫《寰宇访碑录补》亦登六枚,仍沿旧名,题曰印笵,皆不可解者也”[15]。封泥名称在不同学者的认识中来回摇摆。
从目前可见文献看,咸丰二年(1852年)去世的刘喜海在他生前所编的《长安获古编》中,以“封泥”为名著录了“东郡太守章”“东莱太守章”等30枚封泥,但其判断“封泥”名称的过程并不清晰。
1903年(光绪癸卯),罗振玉在《郑盦封泥序》中言:
古泥封于金石学诸品种最晚出,无专书记录之。玉以为此物有数益焉:可考见古代官制以补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证古文字,有裨六书,二也;可考见古艺术,三也。顾传世颇 。此卷为吴县潘文勤公所藏,计官私印三百有四。亟付之景印,以广其传。他家所藏,续有所得,当次第印行之。光绪癸卯正月[16]。
。此卷为吴县潘文勤公所藏,计官私印三百有四。亟付之景印,以广其传。他家所藏,续有所得,当次第印行之。光绪癸卯正月[16]。
在指出封泥蕴含三点价值之前,言其为“泥封”。不过在其所著《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中则名“封泥”[17]。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究竟是称之为“封泥”还是“泥封”,至今学者还在讨论之中,如新近周晓陆先生在系统研究后就指出,应以称“泥封”更为恰当[18]。
1904年刘鹗《铁云藏陶》将封泥单独出来列为一编“附诸陶器之后”,他在该编的自序中对封泥发现和认识的过程进行叙述,并以“泥封”为名加以略释:
泥封者,古人封苞苴之泥而加印者也。封背麻丝粘者往往可见。在昔不见于著录,自吴荷屋《筠清馆金石》始录六枚,称为印 ,误以为铸印之笵也。云:“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估人赉至京师,大半坏裂。诸城刘燕亭、仁和龚定庵各得数枚,山西阎贴轩藏数枚,余不知落何处”。予考《长安获古编》所载,凡二十品,然则刘氏复有续得也。其后蜀中、山左各有所出,为数当日颗,予不能得其详矣。姑以敝藏所有拓付石印,附诸陶器之后,虽非三代文字,然其中官名多为史籍所不载,殆亦考古者之一助云[19]。
,误以为铸印之笵也。云:“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估人赉至京师,大半坏裂。诸城刘燕亭、仁和龚定庵各得数枚,山西阎贴轩藏数枚,余不知落何处”。予考《长安获古编》所载,凡二十品,然则刘氏复有续得也。其后蜀中、山左各有所出,为数当日颗,予不能得其详矣。姑以敝藏所有拓付石印,附诸陶器之后,虽非三代文字,然其中官名多为史籍所不载,殆亦考古者之一助云[19]。
刘鹗不仅在这里著录了148枚“泥封”[20],还明确指出“泥封者,古人封苞苴之泥而加印者也”,指出了封泥的性质。其所言“苞苴”,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如《礼记·曲礼上》:
凡以弓剑苞苴箪笥问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孔颖达疏:
苞者以草包裹鱼肉之属也,苴者亦以草藉器而贮物也。
《荀子·大略》:
祷曰:……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杨倞注:
货贿必以物苞裹,故总谓之苞苴。
在一般情况下“苞苴”多指的是物品。因此从刘鹗的序看,虽他敏锐认识到封泥“其中官名多为史籍所不载,殆亦考古者之一助”,并注意到封泥背面的情况——“封背麻丝粘者往往可见”,但终还是未能将封泥与公私文书的封缄更加直接的联系起来。
光绪九年(1883年)陈介琪所辑《十钟山房印举》收录封泥247枚,无释文[21]。光绪三十年(1904年),吴式芬、陈介琪编辑出版收录封泥达849枚的《封泥考略》。该书分十卷,分以古玺封泥、汉帝信玺封泥、汉朝官印封泥(卷一)、汉诸侯王玺印封泥(卷二)、汉郡国官印封泥(卷三、四)、汉县邑道官印封泥(卷五、六、七)、新莽朝伪官印封泥(卷八、九)、汉臣民印封泥(卷十)进行封泥著录。
该书不仅直接以“封泥”为名,而且对每枚封泥都做了详略不等的考证,较之前诸多著录有了明显进步[22]。而特需指出的是,在《封泥考略》中,还在对“皇帝信玺”的考证下,较详细的对封泥使用方式进行了分析:
《百官志》“守宫令一人”,本注曰“主御纸币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今按,《后汉书·李云传》“尺一之板”注:诏,策也。《汉书·昌邑王髆传》“持牍趋谒”。《原涉传》“削牍为疏”。《外戚传》“手书对牍背”,并注“牍,木简也”。又《周勃传》“吏乃书牍背示之”,注“牍,木简以书辞也”。《说文解字》“牍,书版也”,《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蔡邕传》注同。《史记·匈奴传》“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单于遗汉书一尺二寸。牍及封印皆令广大”。据此则汉时诏策、书疏皆以木简,亦曰板。版均可名牍,皆有封泥。
此封泥色紫,背有版痕,当是以版入中,上以绳缄其口,以泥入绳至版,然后加以封印,外加青囊。囊至两端无缝,以护封泥。如藏玉牒于石检,金绳滕之、石泥封之、印之以玺也。中约署,当是束牍之中而署字也为识也。
《东观汉记·邓训列传》,又知训好以青泥封书,过赵国易阳,……[23]。
他们从文献出发的相关探讨,与后来考古学传入中国后的一系列发现多有吻合。
与此同时,该书第一卷著录的第一枚“古玺封泥”的考释文字,记录了作者敏锐观察到封泥背面所留封缄方式的差异,“泥下有细文,不似版痕,似非施于简牍者。真封泥中奇古之制矣”,这种对封泥正背情况均加注意的著录形式,与之前其它著录相比,当然要更进一步。
宣统元年(1909年),在山东纪王城出土三百余枚封泥,而大约同时,在山东邹县也有封泥出土,二地所出封泥后为罗振玉所得[24]。如胡平生指出,清末动荡之际,受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大谷光瑞派其驻北京的代表寺僧的邀请,罗振玉在带了50万卷图书、3万多片甲骨、数千件碑拓、青铜器及其他文物1千余件后,携王国维等东渡日本。而也就在此时,王国维开始了他之后著名于世的包括封泥在内的国学研究[25]。
据有关文献,综合孙慰祖[26]、周晓陆、路东之[27]、王辉[28]、王伟[29]、杨广泰[30]、郑宇清[31]、吕健[32]等学者既有研究成果,1949年前封泥发现与著录的情况可梳理如下:
道光二年(1822年),蜀地出土封泥,后归刘喜海、龚自珍、阎贴轩等收藏。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吴荣光在《筠清馆金石》中著录6枚封泥,称“汉世印笵子”。
咸丰二年(1852年)去世的刘喜海生前编辑《长安获古编》,著录蜀、长安等地封泥29枚。[33]
光绪九年(1883年)陈介琪在名为《十钟山房印举》实为《十钟山房封泥》中收录封泥247枚。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刘鹗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之二的《铁云藏陶》后单独附出封泥编,著录封泥165枚[34]。
光绪三十年(1904年),吴式芬、陈介琪编辑出版《封泥考略》,收录封泥843枚[35]。
1913年,罗振玉编辑出版《齐鲁封泥集存》,收录封泥449枚。
1924年,陈宝琛编辑出版《澂秋馆藏古封泥》,收录封泥242枚。
1928年,周明泰编辑出版《续封泥考略》,收录封泥454枚;编辑出版《再续封泥考略》,收录封泥320枚[36]。
1931年,吴幼潜编辑出版《封泥汇编》,收录封泥1115枚。
1934年,马衡编辑出版《封泥存真》收录封泥177枚。
1936年,王献唐编辑出版《临淄封泥文字》,收录封泥465枚[37]。
1940年,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刊登了12枚“汉封泥”的正面照片和拓本[38],从封泥的图像看,其中的“居室丞印”为秦封泥。
日人在侵华期间,曾于牧羊城发现“河阳令印”“武库中丞”圆形封泥,后出版的考古报告发表了封泥照片[39]。二封泥今藏于旅顺博物馆,在2000年出版的《辽海印信图录》中发表了封泥拓片、正面照片并介绍了其规格大小,并有简单考释[40]。
二 辨识秦封泥
在封泥发现的早期,不仅封泥的发现数量少,而且封泥的性质也还在探讨之中,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封泥的时代进行如今天这般细致的区分。在开始著录封泥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吴荣光南海吴氏家刻本《筠清馆金石》、咸丰二年(1852年)刘喜海《长安获古编》等著录中,在光绪九年(1883年)陈介琪所辑的《十钟山房印举》、之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刘鹗抱残守缺斋《铁云藏陶》中,或提封泥时代为“汉”,或不言封泥时代而“默认”为汉。
但也确实有学者在这个阶段中开展了封泥时代细化的探索。如国家图书馆藏有光绪八年(1882年)吴大澂编撰的《愙齋所藏封泥目》抄本,共收录80枚封泥的名称。该稿本为吴大澂寄赠陈介琪之物,陈介琪在收到后的次日,就在如“未央卫丞”等19枚封泥下书“伪”字,在“绥远将军章”等10枚封泥下书“疑”字,对共29枚所藏封泥的真伪提出意见。不仅该目将新莽封泥提出单列,而且陈介琪更在“西共丞印”下单写一“秦”字,对这枚封泥的时代提出明确意见,是目前所见首例确定的秦封泥。[41]
当然,虽然如此,当时整个学界对封泥断代开展的分析都甚为有限,而这种情况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吴式芬、陈介琪编辑《封泥考略》才有改观。
在《封泥考略》中,吴式芬、陈介琪设计了一个新的编辑体例,其先是按时代,首为“古玺封泥”,次为“汉帝信玺封泥”,后为“新莽朝伪官印封泥”,之后在不同的时代下按职官地理进行进一步的排序。它的如是排序表明,从释六舟旧藏道光十七年(1837年)汉封泥拓本开始,在经过67年封泥数量和认识的积累后,封泥的研究已日渐成熟。而这种按时代分类型编辑的体例,基本被后来出版的《齐鲁封泥集存》《澂秋馆藏古封泥》《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封泥汇编》等著录所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1年吴幼潜编辑出版的《封泥汇编》中,虽然没有给封泥进行考证,但他将在之前其他著录中列入汉帝封泥的“皇帝信玺”,编列入“古鉨封泥”,并将其排列在了“古鉨封泥”的最后一枚,接下来为“汉朝官印封泥”。这样,虽其没有文字来指出“皇帝信玺”就是秦物,但如是排列所显示出的目“皇帝信玺”为秦物的含义,却甚为明显。
1936年,王献唐在编辑《临淄封泥文字目录》时,首次在“周玺封泥”后,单独列出“秦官印封泥”的名目,将其与“汉朝官印封泥”并列起来。他在“秦官印封泥”下罗列出其判断为秦封泥的封泥,有临菑丞印、临朐丞印、昌阳丞印、芒丞之印、琅邪侯印、左田之印等6枚。王献唐在这里指出:
右封泥印文,皆有阑格,为赢秦印式。其制处于有周,周玺初无阑格,继刻边阑,后于中作直界,又后加刻横划,遂成四格。秦代官印,袭用旧式,无不具阑格。每空一字,字多莫容,则合二字入格。汉初印曹制文,间仍秦制(汉初王国官印,皆无阑格。郡守景帝二年改太守,传世守与太守封泥,俱有阑格、无阑格两种,知中朝亦未一律),后更废除。上印、丞、侯诸秩及郡县名称,汉初与秦略同,殊难为别。惟有阑格封泥,皆出临淄东门外,与汉之无阑格者区域不同。东门外为秦官署旧址,故以所出录为秦制,说详叙文[42]。
这样,在道光二年(1822年)蜀地发现封泥114年后,在释六舟旧藏道光十七年(1837年)汉封泥拓本显示的封泥著录99年后,秦封泥终于从古鉨封泥、汉官印封泥中单独出来。
从上引王献唐在提出“秦封泥”时的判断看,他确定秦封泥的根据,主要还是从秦印而来。他认为,秦封泥的突出特征是封泥有阑格。他明确指出,不同时代封泥的出土地有明显不同。虽王献唐在这里提出的这两点判断依据未见得完全而准确,但从之后在西安相家巷等地大量出土秦封泥的发现情况看,除少数因秦封泥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例”外,根据封泥泥面有阑格和出土地进行判断其是否为秦封泥的方法,依然基本准确。
这样,如果我们从王献唐判断秦封泥的特征回溯,就可以在判断《长安获古编》封泥第5页左的田字格“定陶丞印”、《铁云藏陶》126页上“私官丞印”有竖阑,147页下“承丞之印”、151页下“公车司马”、152页下“乐府锺官”均有田字格等4枚封泥,均为秦封泥。
当然,早在王献唐专列秦封泥之前,已有一些收藏家或学者在进行封泥考释时,指出个别封泥的时代为秦。如1996年孙慰祖在《古封泥集成》序中曾梳理过秦封泥的认识过程,指出《封泥考略》在“叁川尉印”的考释中,指“《地理志》河南郡注‘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此曰‘叁川’,即三川郡尉之印,印篆‘叁’字与《石鼓》同,字又近斯,当是秦印”。认为“具备如此外证条件的封泥为数不多,且完全依附文献也很难免穿凿之失”。特别指出《封泥考略》:
卷六“东安平丞”引《史记·田单列传》徐广注“齐改为安平,秦灭齐改东安平”,遂认为此印“大于汉官印,‘与秦官印大,私印极小’之论合,是秦印也”,其偏差是明显的。东安平两汉均置,此封泥文字风格与秦相去较远,应是西汉中期遗物。
周氏《续考》及《再续》基本上侧重于考证史料,但周书对于秦印的认识似与实际已较接近,如卷一“信宫车府”,云“印文错综,似是秦印也”。
这些释例大致反映了当时封泥断代的方法和认识水平。总体而言,此期玺印断代之学尚属朦胧阶段,研究封泥的学者还未能更多地注意到对其印文形式作时代特征上的归纳排比[43]。
在《古封泥集成》序中,孙慰祖还指出当时已可确认的秦封泥标准品“叁川尉印”“萯阳宫印”“安台左塈”。
2001年,周晓陆、路东之在出版的第一部秦封泥著录《秦封泥集》的《秦封泥简论》中,专列一节“秦封泥认识小史”,梳理秦封泥的认识过程。指出,《封泥考略》中:
“叁川尉印,……当是秦印”,“赵郡左田,……簠斋藏有‘泰上寝左田’铜印,盖一时所制”,“田廥,……疑是秦制”,“怀令之印,……印字是秦篆文,又有十字阑,殆秦物也”,“重泉丞印,……有十字阑,文横读,似秦制”,“屯留,……似秦印”,“博城,……似秦印”,“公印……印文似秦”,“刍状,……秦以前物也”,“王未,……中有阑,亦似秦物”,应当说,这十品的断代是准确的。而同属又将汉代“□(采)铜”、“庐江豫守”、“东安平丞”、“临菑卒尉”、“南郡发弩”、“公孙强印”、“□将士”等封泥误作秦代遗物。又对于秦代的“安台丞印”、“安台左塈”等,不提出具体断代的意见,似误指认为汉武帝时代的遗物。值得注意的是,《封泥考略》中将后世艳称为秦玺封泥的“皇帝信玺”,置于“汉帝封泥”条下,明确表示了断代意见,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一意见是颇有见地的。
以后的一些封泥著录,如周进《续封泥考略》中,正确地指出“信宫车府”封泥“或曰此印文错综,似是秦印也”。然而是书录有其它几枚秦封泥而未识,又误说“司空之印”汉封泥为秦物。总的来说进展并不大。而吴幼潜《封泥汇编》,将“皇帝信玺”置于“古玺封”栏之殿后,“汉朝官印封泥”栏之前,大约表达了视其为秦物的观点,对于后来这枚封泥的评价,影响很大。对于其他十余品曾已确认的秦封泥,他将之统统归于汉代遗物栏中,就秦封泥的认识、研究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44]。
郑宇清系统梳理了《封泥考略》中提出与秦有关的20枚封泥考释文字后,指出《封泥考略》“将封泥归为‘秦’的主要依据为‘印文顺序’、‘印的大小’、‘字体’、‘有阑(即界格)和‘官名不见载’”[45],基本一直都是后来学者判断是否为秦封泥的重要理由。
与任何事物一样,封泥的发现和封泥的认识,是一个互相推进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以目前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封泥断代看,在封泥的著录中,早期蜀地发现的封泥都是汉物,自然不会提出秦封泥的判断(当时也并未认识到它们就是封泥,如前所言,当时尚还断其为“印笵子”)。由于尚处发现的早期,对封泥时代特征肯定了解不多,所以刘喜海不能将关中收获中“定陶丞印”等定为秦物也就在情理之中,刘鹗在《铁云藏陶》中不辨秦物也自不能苛求。
因此,从1904年吴式芬、陈介琪《封泥考略》开始对个别封泥进行时代为“秦”的探讨,到1936年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中最终单列“秦封泥”一目,在这32年间出版的封泥著录,虽无论编辑体例还是时代判断都略有反复,但依然可以看出封泥研究和认识是越来越成熟。所以,封泥的发现和确认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用很长时间从大量的封泥中辨识出秦封泥,就是一个不断探讨与研究的水到渠成的结果。
三 秦封泥的发现与著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之前因日军侵华而全面停顿的考古工作,不仅很快恢复,而且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大。封泥在这个过程中陆续被发现和公布出来。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学术事业的发展,分散收藏在国内外的公、私博物馆、考古机构的大量封泥,以各种形式得以著录出版。无论是新公布封泥的数量和品种,还是各地出版的封泥著录和研究成果,都远非之前可比。秦封泥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惊人的发现。
1954年4月,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工作队对洛阳王城开展考古调查,之后9月至1955年1月、1955年3至4月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进行了发掘,出土了2枚“雒阳丞印”封泥,并发表了其中1枚封泥的拓片[46]。后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中发表了两枚封泥的拓片和正、背照片,均有十字界格,为秦封泥[47]。
1979年4月,辽宁省文化厅文物普查培训班在凌源县安杖子古城遗址发掘的西汉遗存中,于H4中出土封泥18枚,H3出土封泥1枚,共出土封泥19枚,发表11枚封泥拓片。从发表封泥拓片看,除“右美宫左”“右北太守”2枚封泥文字粗壮为汉封泥外,其余“夕阳丞印”“廷陵丞印”“薋丞之印”“昌城丞印”“广城之丞”“白狼之丞”“当城丞印”“泉州丞印”等封泥均有十字界格,当为秦封泥。[48]。后封泥中的13品在《辽海印信图录》中有拓片、照片发表,并有封泥规格介绍、泥面文字考释[49]。
1979年5月,冯永谦、姜念思同宁城县文化馆文物组王维屏对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甸子公社黑城大队古城址进行考古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渔阳太守章”“白狼之丞”“卫多”封泥各1枚,发表3枚封泥拓片,其中“白狼之丞”有十字界格,为秦封泥[50]。
1995年,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内相家巷村南田地中出土大量秦封泥,但封泥在出土后很快就流散于国内外。留在国内封泥的大部分,被后来成立的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路东之收藏[51],并由周晓陆判断其时代为秦[52],流散到澳门珍秦斋的封泥由孙慰祖指出时代为秦[53],殊途而同归,为学界幸事。而销售封泥的闫小平,后将向路东之销售时留下的600余枚品相好的秦封泥,售于傅嘉仪主持的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收藏[54]。
1996年4月,孙慰祖修订再版《古封泥集成》,收录封泥2670枚[55],“增补了部分乐浪出土封泥以及珍秦斋收藏的新出秦封泥等28枚,这是陕西新出秦封泥最初发表的资料”[56]。作为最早关注海外流散相家巷秦封泥并进行研究、著录的学者,孙慰祖《古封泥集成》新版中收录12枚珍秦斋藏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后,使得该书成为内地最早的该批秦封泥著录。
1996年6月,路东之应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邀请举办《路东之收藏瓦当封泥展》,展出路东之梦斋藏彩陶、瓦当、封泥等藏品,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在其中展出[57]。
1996年,吴振烽将陕西历史博物馆历年移交、收藏的来自陕西省文管会发掘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拨交的69枚封泥,进行考释后加以公布,其中部分为秦封泥[58]。
1996年12月26日,西北大学召开“首届新发现秦封泥学术研讨会”,路东之向西北大学博物馆捐赠20品秦封泥,并以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名义向社会公开了秦封泥的重大发现,公布了路东之藏秦封泥的信息和部分品种,引起学界高度重视[59]。
1997年初,周晓陆、路东之、庞睿将路东之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收藏秦封泥在整理后公布了154种封泥的拓片和释文[60]。
1997年1至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得到傅嘉仪获得的相家巷秦封泥准确出土地信息后,在程林泉的带领下在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相家巷村南发掘185平方米,清理40个遗迹单位,共出土封泥11347枚,是迄今为止一个遗址出土封泥数量最多的地点。据介绍,发掘中最重要遗迹有3个:H3出土封泥2266枚、H25出土2833枚、M3出土2266枚。该次发掘的资料尚在整理之中。经初步整理,与职官有关的封泥7600枚,与地理名称有关的1300枚,其它240多枚[61]。
1997年4月,倪志俊在《书法报》上公布了相家巷秦封泥的准确地点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收藏秦封泥的相关情况,公布了25枚封泥的拓片,并指出该批收藏品相完好,可以纠正之前少数因残缺而致误的封泥释读[62]。
1997年6月,罗小红在《说古道今》上介绍了相家巷秦封泥发现的具体情况,并公布了25枚封泥的拓片[63]。
1997年7月,傅嘉仪、罗小红在《收藏》杂志介绍了汉长安城内新发现秦封泥的相关情况,刊发49枚封泥照片[64]。
1997年8月,任隆以考释的形式,刊布了收藏在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秦封泥114种[65]。
1997年10月在西安终南印社的内部刊物《终南》的第1辑上,崎岖刊发《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简介》和“永巷”“右丞相印”等51枚封泥的拓本[66]。
1998年2月,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继续刊布了62品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藏秦封泥[67]。
1998年6月,任隆再以考释形式公布收藏于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的秦封泥[68]。
1998年9月,路东之出版《路东之梦斋秦封泥留真》原拓秦封泥100品[69]。
1998年10月,路东之在日本篆刻美术博物馆举办的封泥展览上,做了《封泥收藏与研究的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70]。
1999年1月,傅嘉仪出版《篆字印汇》,其采择来源广泛,“手钤本、散页、新出土玺印、封泥瓦当,及未发表者占重要比例”,其中“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代封泥”即在其中,成为相家巷秦封泥藏品的一次集中著录[71]。不过受体例限制,秦封泥散见于不同字头,使用起来并不方便。
1999年,孙慰祖将新发现的秦汉官印、封泥进行汇释[72]。
1999年12月,傅嘉仪编辑出版《历代印匋封泥印风》,收录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257品秦封泥拓片[73]。
2000年5月,周晓陆、路东之在全面公布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藏秦封泥的基础上,结合之前谱录中著录的秦封泥,整理出版了第一部秦封泥的专有谱录——《秦封泥集成》[74]。该书除集中刊布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封泥外,还对封泥本身的相关信息开展认真梳理,对封泥背后痕迹所反映出来的封缄方式的探索细致而深入。这种强调和彰显封泥本身考古学特征的做法,与作者长期从事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教授与科研的经历直接相关。
2000年4至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在之前盗掘出土秦封泥的相家巷村南田地进行发掘,发掘面积500余平方米。该次发掘获得封泥325枚,共100多种,从地层学上确定了封泥的时代为秦。发掘资料在快速整理后在2001年及时发布,同期刊发了刘庆柱、李毓芳的研究文章[75]。
2000年杨广泰主编《秦官印封泥聚》,公布了其收藏的秦封泥新品。[76]
2000年,王辉在发表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封泥的同时[77],并在其出版的《秦出土文献编年》中对之前已知秦封泥进行了集中分析[78]。
2000年,萧春源在《珍秦斋藏印·秦印篇》中发表了其收藏的秦封泥12枚,同时发表了相关封泥的正背照片[79]。与1996版《古封泥集成》对比,《古封泥集成》刊发拓片的“居室丞印”“中羞丞印”“安台丞印”3枚不见于是书,是书中刊布的“少府工丞”“咸阳丞印”2枚不见于《古封泥集成》。
2001年8月,周晓陆、刘瑞对新见秦封泥的地理内容进行考释的同时将封泥信息进行公布[80]。
2001年9月,许雄志出版《秦印文字汇编》。该书虽名秦印,然其采择时即包括封泥[81]。
2001年10月,傅嘉仪、王辉对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所藏秦封泥在公布的同时并加考释[82]。
2001年12月,王辉对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中的若干品种进行考释[83]。
2002年7月,周晓陆、陈晓捷通过《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公布了新发现的有关中央职官的秦封泥,并加以考释。[84]
2002年10月,周晓陆等发表《秦封泥再读》,对部分新的秦封泥资料进行公布。[85]
2002年10月,傅嘉仪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收藏秦封泥为主进行了结集出版,共刊布封泥432品,其中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341品公布正背拓本,并有释文,同时收录发表于《秦封泥集》的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藏34品,并收录早期谱录中秦封泥附录57品,多有简略释文。[86]
2002年,刘庆柱在对相家巷新发掘的封泥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同时发表了一些在之前《考古学报》中未加公布的封泥拓片[87]。
2002年,周晓陆、陈晓捷发表了在北京新见的秦封泥品种并做考释[88]。
2002年,周天游、刘瑞整理了之前已发表的419种秦封泥品种,并结合新公布的张家山汉简对秦封泥的释读问题进行了研究[89]。
2002年12月,孙慰祖出版了作为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之一的《中国古代封泥》。该书在详细介绍了上海博物馆藏封泥的来源后,大量发表了上海博物馆藏封泥的精美拓片及正反面彩色照片,并收录了上海博物馆2001年入藏的部分相家巷遗址出土秦封泥[90]。
2002年4至11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进行里耶古城发掘的过程中,在出土大量简牍的J1中出土二百多枚封泥匣,匣上少数有文字。出土“有封泥十多枚,多残破。圆形印面,其上的文字系胶泥半干时以玺印戳上,因废弃时偶然被火烧后陶化而得以保留,背面不规则,直径2.6厘米许,厚不足1厘米。内容有□陵□印、□庭□马(洞庭司马)、酉阳丞印、酉□丞□等”。后记述出土封泥“数量较多”,“原置于来往邮件的封泥匣内,多破碎不易收集”,考古报告介绍了其中10件封泥的情况,发表了封泥摹本[91]。
2003年,王辉考释了新发现的三枚秦封泥[92]。
2003年,路东之出版《古陶文明博物馆藏战国封泥》原拓本[93]。
2003年2月,徐畅在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先秦玺印》中,在“战国公玺与印迹”下专列“秦印与封泥”,收录了208枚秦封泥的拓本[94]。
2004年12月,日本艺文书院出版《新出相家巷秦封泥》,收录了相家巷出土秦封泥250种的正反照片和拓片,其中“泰史”“南郡府丞”“蜀大府丞”等为之前所不见[95]。
2005年1月,伏海翔出版《陕西新出土古代玺印》[96],在刊有“华阳丞印”“左司空印”封泥的彩色照片外,还有187枚封泥的拓本和释文。该书虽未介绍封泥来源,但从封泥拓本看,其基本为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收藏。
2005年,周晓陆、陈晓捷、刘瑞、汤超、李凯等对流散在北京等地的新见秦封泥进行考释[97]。
2005年12月,马骥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在西安新发现的21枚秦封泥品种,并探讨了秦封泥的断代问题[98]。
2006年,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六村堡村内的东西路南侧发现秦封泥,该地与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地相距约600米[99]。
2006年6月,陈晓捷、周晓陆发表《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公布了50品文雅堂藏秦封泥,多为新品。[100]
2007年,李晓峰、杨冬梅在秦封泥发现的推动下,将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的带界格封泥进行了专门的公布和考释[101]。
2007年,傅嘉仪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收藏秦封泥为基础,将“周晓陆、路东之先生的《秦封泥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辉先生关于秦封泥论述,以及作者本人关于秦封泥的浅述合编而成”的《秦封泥汇考》出版。在该书自序中,傅嘉仪在对秦封泥发现经过简要叙述后,从文字演变、“丽山食官”封泥线索体现出的时代性、“泰厩丞印”“中厩丞印”“小厩丞印”等多见于秦始皇出土陶文的职官名、“废丘”“废丘丞印”等文献记载汉初即已改名的地名等四个方面加以探讨。书中对秦封泥有简略考释,书后彩版为230品封泥的拓片、正、反面的彩色照片[102]。
2008年3月,路东之出版《问陶之旅》,发表了在《秦封泥集》之后陆续收集的战国、秦和汉代封泥[103]。
2009年6月,王玉清、傅春喜出版《新出汝阳郡秦汉封泥集》,公布了在河南平舆出土的汝阳郡封泥554枚的拓片(多为汉封泥),部分封泥同时公布了正反照片[104]。
2010年,周晓陆出版《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其虽名玺印集成,然对已知封泥资料同样进行了集中收录,蔚为大观[105]。
2010年,郭富春在出版的《大连古代文明图说》中公布了1枚封泥的照片和拓片,有十字界格,为秦封泥[106]。
2010年11月,西泠印社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办“新出战国秦汉封泥特展”和“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配合展览出版的图录收录了战国封泥6品、秦封泥111品,西汉(含新莽)封泥135品的正反照片和拓本[107]。
2010年,杨广泰出版《新出封泥汇编》,共收录了其个人收藏的7800方1272种封泥,“约近已知存世封泥之半,所收封泥拓片百分之八十为首次刊布”,包括战国封泥11种、秦封泥434种、西汉封泥361种、平舆出土两汉封泥372种、新莽封泥94种,其中507种为首次发表,占全书全部的40%。该书不仅是《古封泥集成》后最大规模的封泥著录,更是新出封泥资料的一次大汇聚[108]。
2011年4月,许雄志将自己收藏的战国秦汉封泥结集出版。根据来源不同,分别为河南新蔡战国封泥49枚、西安相家巷秦封泥28枚、临淄西汉封泥19枚、平舆秦汉封泥206枚、未名出土地域封泥9枚,各封泥均有正反面照片和拓片,印制精美[109]。
2012年4月,周晓陆出版《酒余亭陶泥合刊》,公布了他2001年收藏的204枚“泥封”的拓片,其中不少“是未曾面世的孤品”[110]。
2012年底,《唐都学刊》发表20枚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的彩色照片[111]。
2013年,周晓陆、陈晓捷对文雅堂收藏的封泥加以公布和考释[112]。
2014年9月,秦陵博物院入藏1100余枚秦、西汉、新莽、东汉封泥及燕、齐陶文。据介绍,该批封泥原为杨广泰收藏,由赵旭捐赠于秦陵博物院。王辉发表了其中327枚汉封泥的拓片、释文与考释[113]。
2014年,王伟对博士论文修订后出版《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114],系统收集、梳理了之前已发表秦封泥资料,并对秦官制、宫室、苑囿、陵寝及郡县等开展综合研究。
2014年,王辉、王巧英公布了数枚文雅堂收藏秦封泥[115]。
2015年,王伟考释公布了文雅堂收藏的秦封泥20枚[116]。
2015年5月,西泠印社美术馆举办《古代封泥精品展》,展出历代封泥400品,后出版的图录选择了其中200品的正反放大照片和原大拓片并附释文,在封二、封三等刊录了48品残泐封泥照片,为封泥的缀合工作提供了宝贵资料[117]。
2015年7月,杨广泰出版《新出陶文封泥选编》,公布了其收藏的战国封泥3种、秦封泥246种、汉封泥228枚、新莽封泥93种,以拓片为主,个别封泥有正反面彩色照片[118]。
2015年12月,庞任隆编辑出版《秦封泥研究》,将之前已发表的20篇秦封泥研究文章进行了集中收录,并提供了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100枚秦封泥的统计表,其中2件封泥时代注明为“战国”[119]。
2016年,蔡庆良、张志光在出版的《秦业流风:秦文化特展》中公布了之前在西安南郊贾里村大墓发掘中出土的“内史之印”封泥[120]。
2016年,在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编著出版的《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中,刊发了里耶出土的“酉阳丞印”封泥的照片,并与出土的封泥匣并排放置[121]。
2017年,王伟公布了文雅堂收藏的地名封泥15品[122]。
2017年8月,魏杰在《金石研究》创刊号上公布了其所藏的“高章宦丞”“都水丞印”“骑马丞印”“内官丞印”等10品秦封泥的拓片和彩色正背照片[123]。
2017年10月,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在《书法》上刊布了馆藏236品封泥精品的彩色照片[124]。
2018年8月,许静洪、许云华将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收藏封泥资料加以刊布,包括战国封泥1品、秦封泥4品、汉封泥97品,均有正反照片、拓本和释文[125]。
2018年李振洲介绍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收藏的20枚秦封泥的彩色照片和释文[126]。
2018年,任红雨出版了由刘庆柱、王辉作序的《中国封泥大系》。该书汇集2017年6月之前作者所见的63种封泥谱录,还有作者自己搜集的珍稀、孤本封泥原拓5336枚,共辑录封泥拓片15177枚,6347种。该书的编排以时代为经、音序为纬,分战国封泥、秦官印封泥、秦私印封泥、两汉官印封泥、汉私印封泥、新莽官印封泥、新莽私印封泥、汉后官印封泥、唐官印封泥等9目,其中战国封泥242枚,106种;秦封泥5485枚,2085种;汉封泥7942枚,3235种;新莽封泥1487枚,902种;汉后官印封泥7枚,7种;唐官印封泥14枚,12种,成为自封泥发现以来收集封泥数量、品种最多的封泥谱录,是封泥著录的新一代的集成之作[127]。
2019年,许卫红、张杨力铮、赵震、狄明在《陕西省咸阳城府库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公布了遗址发掘的秦封泥1种[128]。
2019年5月,孙慰祖在《问印》创刊号上发表《新出封泥撷珍》,发表了12枚秦至唐封泥,不仅多枚封泥为首次发表,而且封泥的拓片和照片均甚为精美[129]。
2019年,许雄志出版《鉴印山房藏古封泥选粹》,辑录战国秦汉官印及汉私印封泥254枚的拓片,其中来自新蔡战国封泥50枚、来自河南郡封泥54枚、弘农郡封泥50枚、汝南郡封泥50枚、汉私印封泥50枚[130]。
2019年,李超介绍了收藏于西安博物院的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相家巷发掘秦封泥30余枚。在该文表二中,还显示出西安博物院所藏“桓段”“公车司马”“苏段”“泰匠丞印”“美阳丞印”“中厩丞印”“谒者丞印”“咸阳亭丞”“诏事之印”等9枚西安博物馆藏秦封泥的名称,并在注中介绍原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的绝大多数秦封泥,已在2010年后由西安含光门遗址博物馆所收藏[131]。
四 秦封泥集存
从1882年陈介琪提出“西共丞印”时代为“秦”至今已有137年,从1904年吴式芬、陈介琪《封泥考略》辨识出个别秦封泥至今已有115年,自1936年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单列“秦封泥”目至今也达83年。在长达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学界秦封泥研究的成果日益丰富,相关认识日益成熟。秦封泥蕴含的学术价值,也在不断的研究中得到阐发。
从封泥发现情况看,在1997年相家巷遗址秦封泥大量发表之前,已知秦封泥的数量和品种都非常有限,学者以秦封泥为对象开展的研究自然不多。多数情况下,学者提到秦封泥都仅是封泥史中的一笔带过,极少以秦封泥为专题进行研究,更遑论秦封泥研究专著。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因此在1995年西安汉长安城相家巷遗址大量出土秦封泥后,在巨大新材料的推进下,秦封泥研究的情况得到极大改观。
1995年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出土,如李学勤先生所言,与甲骨文一样,不仅一开始并非科学发掘,而且在出土之后还很快流散。不过可喜的是,在相家巷秦封泥流散的过程中,很快孙慰祖先生在澳门鉴其时代为秦,路东之先生收藏的封泥也经周晓陆先生确认为秦。虽各自“闭门造车”,但最终“出门合辙”,一南一北可称为学界幸事。
之后,在周晓陆先生的大力推动下,1996年12月26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召开了“首届新发现秦封泥学术研讨会”。巨量秦封泥的发现,马上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要和积极评价。而更加可喜的是,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得到傅嘉仪提供的封泥出土准确地点信息后,迅速对其进行发掘,获得更加巨量的发现。错失了之前收藏秦封泥机会的傅嘉仪先生,也从闫小平手里,将其销售路东之时留下来的精品封泥,尽纳于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
这样,虽相家巷秦封泥在出土后即有流散,但由于确认及时,绝大多数秦封泥还是都留在了国内,留在了国内的公私博物馆中,避免了再次流散和失落的可能。于是,秦封泥才能在之后的短短一两年时间里,以巨大的数量和远超人们想象的丰富内容,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一样,一次次的震撼着学界。
伴随着各家收藏的庞大到远超人们想象的秦封泥数量和品种的公布,以及各项研究成果的不断深入,关于秦封泥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在今天看来已非常惊人。甚至可以说,20年多年来学界开展的秦封泥研究的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过了经一百六十余年积累和发展的汉封泥研究,成为封泥研究中最重要的方向和内容。
关于秦封泥释读或公布的情况,前文已进行了梳理,而从1995年西安相家巷秦封泥发现、1996年底西北大学召开学术会议公布秦封泥发现的消息至今已经20余年的秦封泥研究情况,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综述和评价。如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的发现与研究》[132]、周晓陆《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与初步研究》[133]、王辉《秦封泥的发现及其研究》[134]、《古封泥的发现、著录及其研究概说》[135]、杨广泰、路东之等等。而我也曾以《1997——2001年秦封泥研究概况》[136]和《1997—2002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为名[137],对2002年之前的秦封泥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在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在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王辉《秦文字通论》的相关章节中,也都对秦封泥发现与研究情况进行学术史梳理。在《秦封泥集》出版后学者对其进行积极评价的同时,也对秦封泥研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期待[138]。近年来南京大学崔璨还针对性的对十年来的秦封泥发现和研究情况进行了整理[139]。
从现有的研究情况看,秦封泥研究在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的同时,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1,目前尚有巨量封泥有待公布。从现有信息看,最大一批秦封泥在出土后收藏于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数量多达一万余枚。但遗憾的是,该批封泥虽近年已启动整理,但科学的公布尚须时日。
2,在已公布秦封泥中,多数仅发表封泥泥面拓片,少数公布时发表封泥正背面照片,造成很多封泥泥背情况难以了解。封泥资料的完整性严重不足,给流散封泥的辨伪及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带来巨大困难。
3,封泥易碎,相家巷出土秦封泥在发现的早期流散各地,已发表的封泥以完整品为主,残碎品发表有限,使得同地出土秦封泥本该开展的缀合研究迟迟未能顺利开展。
4,在封泥发表时,往往存在将已有谱录发表封泥再行刊发的情况,致使封泥的发表数量与存世数量难以一致,使得从数量统计角度分析相关问题的设想难以顺利开展。
5,发掘品外的私人藏封泥有着多次转手的情况,其流传信息往往并不公布。因此同一封泥就会出现多次、多家著录的情况,而且由于目前用于传世和发表的封泥拓片,原本就是一个很容易造成差异的手工操作,故在不同藏家不同拓工拓制手法轻重不同的操作下,在对封泥泥面外缘不同的取舍下,很容易的就出现了不少同一封泥的差异性拓片,而很容易让人以为其是多枚封泥。
6,不少私人藏封泥还往往以传统的原拓形式,以百本甚至几十本的极少的数量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公布所藏封泥品种等信息。这种原拓出来的封泥拓本,数量稀少而其价甚昂,严重影响到封泥的传播与研究[140]。
7,由于封泥藏家众多,封泥发表途径自然多样,致使迄今为止发表秦封泥,大量散在了各种期刊、报告、报纸、图录,学者使用起来当然的非常不便,甚至很多已发表多年的封泥要在很久之后才能渐为人知。
在上述存在的七个问题中,后面几个问题都与封泥发表的状况有关,并随着时间的发展和越来越多封泥的发表,日益严重的影响着秦封泥研究的顺利推进。
因此,为完成2014年申报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封泥分期与秦职官郡县重构研究”(14BZS017)研究,为推进作为子课题负责人而参加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14ZDB028)的相关内容,从2015年开始,我陆续将之前收集的秦封泥资料进行查重补缺,并重点收集了十余年来新近出版的考古报告、封泥图录及各种图书杂志,希望获得一份全面的秦封泥目录,以便自己设想的相关研究能顺利推进。到2018年秋,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秦汉三辅地区建筑研究与复原”(18ZDA181)获批,这样含大量秦代建筑职官、宫苑名称的秦封泥,也就自然的成为了该课题研究的一部分内容。
于是我就将之前已整理的资料,根据新的需要做了重新梳理,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等文献及学者研究成果进行了排序。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以下一些具体的考虑:
首先,由于秦封泥在发现之后的快速流散和不断倒手,造成很多封泥藏于多家并多次著录,造成封泥发现数量的统计一直非常困难,因此我就重点开展了对现有封泥图像的查重去重。即,在收集到封泥图像后,将不同时期、不同报告与谱录发表的封泥正面照片、背面照片和拓片编在一起,然后据封泥拓片、照片等所显示出的图形信息进行判读,以确定这些不同的封泥拓片是否来自同一封泥,以便开展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需解释的是,目前我们在本书中所见到的,虽已是经多次斟酌去重的结果,但事实上一直到校对的过程中,我还偶尔的发现了一些之前的遗误。我深深的认识到,查重去重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要判断封泥是否重复,固然一方面是个人眼力高低和究竟该如何取舍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则是与目前所见封泥的拓片原本就是纯手工操作有关。
众所周知,在封泥拓片打制的时候,在对边缘如何取舍,在用浓的还是用淡的墨,手法究竟是轻是重的差异,以及作为拓片载体的纸的差异等等,都会在我们于不同期刊杂志图书等见到的拓片上产生有不同的体现。而且,需说明的是,与碑刻拓制拓片会损失石碑一样,虽封泥易碎,打制拓片的拓工肯定会非常的轻巧。但事实上无论如何的小心,在拓片的制作过程中、在封泥的保管过程中,都会给封泥造成一定的损伤。因此也就使得同一封泥的前后不同时间打制的拓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可视性差异,使得在去重时就很难取舍。
以“代马丞印”下的2号、5号封泥为例,现在两个号下分列的两个拓片的出处不同,也都有一定差异,但通过与封泥照片的比较,当可确定其原应为同枚封泥所拓。而在“北宫宦臣”14号内的同一封泥的三个拓本,外缘均有明显差异,但实际上的封泥却只是一个。“雒阳丞印”下的5号封泥,我们已见到2个外缘差异明显的拓片,在通过与照片比较后,可将其断为同枚。当然,在“咸阳丞印”下109号中罗列的两个差别很大拓本,是施谢捷先生在研究中敏锐注意到其应来自同一封泥;不过,“中厩丞印”下33号中罗列的两个拓本,施谢捷先生认为33b是封泥原状,33a是利用33b和其它封泥拓片的拼缀物。不过从该发表的封泥照片看,此封泥原物完整,并没有拼缀的迹象。所以从拓片和照片看,我判断33a是最初打制拓片,33b是封泥“丞”字出现损伤后打制,自然33c的照片也就是早期拍摄。类似因封泥模泐而形成不同拓片的情况,从“走翟丞印”下9a和9b的拓片也可看出[141]。所以,从封泥拓片、照片的对比看,照片在给封泥进行去重过程中的作用甚为关键。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虽早在1930年代北京大学《封泥存真》中已开创将封泥拓片、正、背面照片一起出版的“完美”体例,但在至今为止已发表的秦封泥资料中,封泥照片发表的情况一直相当有限,这就使封泥的去重工作面临着很多困难,不少封泥从拓片看似是一枚或有区别,但如果没有照片的核验,就不甚完美。
因此,在种种实际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在一时还不能如数目验各地所藏封泥实物的情况下,要判断所见到缤纷的拓片究竟是不是同一枚封泥所拓,也就存在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加之不同时期不同厂家在拓片制作印刷品的过程中,还存在了各种想象不到的印制差异,也使看上去简单的去重工作面临着更复杂的困难。
因此,虽在整理和校对的过程中,我已尽力来做查重去重——当然做这个的初衷是我自己切实想知道迄今为止一共出土和发表了多少封泥,而每种封泥又有多少不同个体——特别是对于那些数量多达几十个的品种就更是如此,并将那些差异较大的拓片分别罗列,但想来在本书印出后,眼亮的师友肯定会在目前所罗列的图像中找到不少应去而未去的重复拓片,需今后不断修订。当然,无论是眼力不足还是看多而眼花,都并不能减少其中必然存在的种种不足。但现所看到的,确实是在庚子春节因抗疫而出现的史无前例的长假闭关期间,自己尽力校对后能所达到的结果——最后关头新见到的施谢捷先生论文当然让我新发现了几个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其次,由于大量秦封泥发表的信息并不完整,以及藏家藏品的来源也多未公布,而秦封泥时代的判读本身就是一个学术难题,所以在对于哪些是秦封泥、哪些不是秦封泥,也很难有一个统一标准和学者共识。当然,无论是秦的职官地理,还是秦的印章制度,本身都是随着秦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发展的制度。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秦封泥,也自然是这一制度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这里收罗的秦封泥,肯定在时代的判断上会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具体的排序和归类上也会有不同看法——这是学术研究中很正常的事情,但如这些对秦封泥认识上的疑问和不同意见,是通过本书的罗列“放在一起”后而凸显出来的话,那多年收集和整理的目就已达到了不少。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收秦封泥的时代,并不限于短暂的统一秦,而是上起战国晚期,少数延续到西汉,大体就是1997年初李学勤先生在西安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后提出的秦封泥的时间范围。而既然我将这些封泥收集在一起,自然意味着在我看来,它们的时代应该为秦——当然这里所谓的秦也是指上述的时间范围。
我判断其时代为秦的根据,一方面在此之前所收集到的绝大多数封泥的时代已有学者判断为秦的结论,一方面则是自己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还进行了一些重新的判定。而我开展进一步判定的依据,一是1996年西安相家巷秦封泥发现之后孙慰祖先生在澳门、周晓陆、路东之先生在西安分别从文献记载和封泥印章制度方面总结的秦封泥特征,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队在汉长安城遗址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秦封泥后,刘庆柱、李毓芳先生总结出的秦封泥特点,同时还考虑了多年来学者在秦陶文、秦印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大体而言,应是一个综合的判断。
整体而言,这里收集的中央、地方类职官封泥的时代,可能争议较小,但具体到某个封泥则应会与之前的意见有所不同,但限于体例在这里无法一一说明,只能另寻机会解释。当然,这里的判断肯定会有不少错误,同样需要今后不断修正。
第三,在秦封泥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当然的还见到了数量较多的乡亭部和私印吉语封泥。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些封泥,一段时间里让我非常纠结。从资料完整性看,当没有任何不收的理由。但从实际情况看,特别是在目前秦封泥断代研究的进展看,其实我们很难给大部分乡亭部、私印吉语封泥一个如前述中央、地方职官封泥那样较明确时代为秦的判断。
从湖南里耶发出土的秦代简牍中,我们见到规模庞大的人口数量甚至超过当时很多县的“贰春乡”等乡级机构。因此从管理角度看,秦乡有印应无问题。在传世和出土封泥中已有不少例证,所以发现和存在秦乡亭部封泥应合情合理。当然,据文献记载,汉高祖刘邦在起义之前任秦的泗水亭长,在之前公布的秦封泥中还有数量较多的“咸阳亭印”封泥,明确表明秦亭有印、有亭印封泥。
据目前所见资料,在秦统一过程中、统一后,秦王朝都采取了一系列包括印章制度在内的制度性变革——在目前所见封泥和出土秦简牍中都有切实反映。但从制度变化的实际情况看,由于秦祚甚短,秦统一过程中、统一后采取的这些变革,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县级以上职官,至今还没有见到明确的在乡亭部和私人印章方面进行强力变革的资料。因此,对数量较多的传世乡亭部和私印吉语封泥究竟该如何断代,就成为一个甚为困难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中,比较而言,私印封泥的情况更加复杂。比方说如建秦的嬴政、李斯,建汉的刘邦、张良、萧何等人,他们有的生于战国晚期,长于秦,有的还在经过短暂的统一秦后,灭秦而立汉,成为汉人。因此,如他们自己使用的私印一直未变,那其不同时间里用该私印抑制的封泥,在被我们发现并放在一起后,是不是就一定能截然的分开?是不是能更进一步的指出它们究竟是战国封泥、秦封泥还是汉封泥?我想,这是目前还难以解决的难题。
当然,在经过一系列痛苦的纠结后,我最后还是决定把乡亭部、私印吉语封泥与之前的中央和地方职官封泥收到了一起,希望能通过现在的工作,能在将其与其他封泥放在一起后,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些许便利。如读者能从中梳理出更多秦乡亭部、私印吉语封泥的特点,那我们的目的就也已部分达到。
将现有的这些封泥收集到一起的依据,一方面是明确的出土品中的乡亭部和私印封泥,一方面是之前学者已指出其时代为秦,一方面则是拥有与前述两类封泥风格相似的特征。而正由于对乡印和私印该如何安置上的犹豫不决、来回摆动及标准难定,因此同我尽量保证没有大的遗漏的中央和地方职官封泥的收集情况相比,乡印私印封泥的缺漏和不足肯定会更多一些。取舍之间,肯定会存在因误判而造成的误入、误删,今后当在大家的关注中陆续修正。
当然,由于目前在乡亭部和私印吉语封泥时代的判断上确实存在很多不定处,因此本书所收此类封泥的时代,自然就比前述中央和地方职官封泥的时代还要宽泛。所以,我把略有根据且有少数断代依据的乡亭部封泥列放在中编的郡县封泥之后,而把私印吉语封泥则直接列为附编——对专门从事印章封泥研究的学者而言,这里收集的私印吉语封泥肯定有很多需不断改进的不足。
第四,我们虽然了解,目前收集和整理的绝大多数秦封泥,都是在考古发掘之外藏于公私藏家的流散之物,但是在目前大多数秦封泥仅以传统的拓片形式进行发表,封泥照片的发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在无法一一目验封泥实物的情况下,在秦封泥因不断打制拓片而出现较多形态变化的情况下,单从拓片而对这些封泥进行真伪的分别就存在着很大困难。
因此,在这里呈现的九千多枚封泥中,虽据封泥形态和内容,我认为其中的大多数应为真品,但也确实有极个别封泥无论从字体结构还是从其上职官地理的名称上看,都那么“与众不同”,其所记载的职官还不见于文献,有可能为伪品。对这种情况,我虽心中惴惴,但依然还是把它们也收纳了进来,免得因一个自己“智子疑邻”的误判,而使一些可能非常重要的信息得不到学者注意,造成学术研究的损失。而我,也希望能通过对这些封泥的集中收纳,在将其与其他封泥放在一起后,让大家从更全面的整体上,能在今后开展进一步的甄别和研究,并逐步将其中可能存在的伪品排除出去。
第五,虽然从王献唐开始多数学者已多次强调性的提出,十字格(含日字格)的泥面形制应是秦封泥的主要外在特征,而从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的情况看,这样的认识当然无误。但是从多年来秦陶文的发现情况看,虽有部分的陶文确实存在十字界格,但也有更大量的陶文没有界格存在。从“大匠”职官封泥的发现看,在秦封泥中我们看到了有界格的“泰匠”“泰匠丞印”封泥,但也存在着没有界格的“大匠”和“大匠丞印”封泥。按我的理解,“泰匠”的写法应是在统一过程中或统一后的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出现,之前的写法应为“大匠”。也就是说,“大匠”早而“泰匠”晚。
但从陶文发现看,我们迄今为止在秦始皇陵、秦咸阳、秦阿房宫遗址、秦废丘灋丘所在的东马坊遗址、秦汉甘泉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等发现的,却只有“大匠”陶文,从未发现“泰匠”陶文。而且,已发现的“大匠”陶文的文字,又与半通的“大匠”封泥高度相似。
因此,我只能认为,虽在秦统一过程中和统一后,更名的措施确实采取了不少,很更改的范围却还有不少控制或宣传不足。以“大匠”而言,当时只是更改了上层的负责主管官员所使用的印章,而下层具体生产时使用的用在建筑材料上戳印的印章,还依然如故。
这也就意味着,有十字界格的“泰匠”与没有界格的“大匠”印章,虽确有早晚,“泰匠”晚而“大匠”早,但实际在“泰匠”出现后“大匠”还继续存在,二者并没有实际的截然取代关系——虽从我们一般认为的制度上“泰匠”出现后即应销毁“大匠”写法的印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秦祚甚短,制度化变革或设计不周或推行的不如人意,因此在进行封泥图像编排时,我就放弃了曾设想在同一封泥下以形制差异进行前后排列的做法(曾试验着做过一些封泥),于是也就有了现各封泥名目下各种写法形制的封泥交错分布的情况。我想,在秦封泥断代工作不断取得成果,对秦的制度和实施情况取得更多认识后,虽然复杂但更接近于当时实际情况的,据封泥早晚进行的排列,应该可以实现。而现在我所提供的,只是一个用于大家批判和修改的底子而已。
在经过了来来回回的反复“折腾”和一系列的痛苦的取舍、去重之后,共集含残封泥、未释封泥、未发表图像封泥等各种情况在内的中央与地方官印封泥1843种8531枚、私印封泥499种675枚、吉语封泥6种6枚、无字封泥5枚、特殊封泥1枚,合计2350种9218枚。
最后需要解释的是,称为《集存》,取自于罗振玉、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并期待更多秦封泥的发表。
秦封泥的发现和公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更多秦封泥的发现和发表,会使进一步开展封泥资料集存与研究成为可能。
希望在这一让人感到痛并快乐的过程中,我们能不断获得新的收获。
[1]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上编《秦封泥简论·古玺印与封泥》,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 (东汉)刘熙:《释名》,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8页。
[3] (东汉)蔡邕:《独断》,作者待刊校本,下同。
[4] 《文选·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首》注引《独断》:“玺,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文选·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首》注引《独断》:“玺,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来,签字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也。”《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之言亦无此八字。又:孙诒让《札迻》卷上:“抱经堂丛书本”注曰:“旧有‘天子玺以玉,螭虎纽’八字。案:不当间侧在此,且其文详,当别为一条,今补于后。”孙诒让案曰:“‘天子玺’八字,《左传·襄二十九年·正义》及释慧琳《华严经音义·三》引并在‘信也’下,则唐本已如此,似不应移后。‘以玉’,《左疏》作‘白玉’,《汉旧仪》同。”孙诒让例为唐本,但《文选》注、《汉书》注均早于唐,故删之。
[5] 孙诒让《札迻》:案:“名”,《左传疏》引作“民”,与《汉旧仪》同,是也。当据改正。又案:“《华严经音义》引此书云:天子之玺,以螭虎钮。古者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玺’。秦以前诸侯、卿、大夫皆曰玺。自兹以降,天子独称,不敢用也。秦王子婴上高祖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即寿且康’,此印章古名玺,即今谓检文也。”自秦王子婴以下,今本无。或慧琳据他书增益,非蔡语。所引于今本上下文多譌异,附录于此,以备校覆。
[6] 今从《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独断》(33页)。“抱经堂丛书本”作“天子玺以玉,螭虎纽”,校:“此句从上移此。案《光武帝纪上》注引作‘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此下二十六字亦据所印补。”
[7]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上编《秦封泥简论·古玺印与封泥》,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8] 赵平安:《汉简中有关印章的资料》,《秦西汉印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131页。
[9] (清)吴荣光:《筠清馆金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海吴氏家刻本。童衍方收藏的释六舟旧藏汉封泥拓本册中有戴熙(字醇士)跋“严道橘园”封泥时云,“西人赉售于都,不常有,有则数十枚,道光十年前未尝有也”,表明封泥从1822年出土,要在近8年之后的道光十年(1830年)左右才传至京师。童衍方:《释六舟旧藏汉封泥拓本册概述》,《西泠印社》2008年8月版(总第18期),第37页。
[10] 孙慰祖:《古封泥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1] 童衍方:《释六舟旧藏汉封泥拓本册概述》,《西泠印社》2008年8月版(总第18期),第37—46页。严格来说,此为未曾出版的拓片册,和成书印行的《筠清馆金石》还是有较大差距。
[12] 童衍方:《释六舟旧藏汉封泥拓本册概述》,《西泠印社》2008年8月版(总第18期),第37页。
[13] (清)吴荣光:《筠清馆金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海吴氏家刻本。
[14] 童衍方收藏的释六舟旧藏汉封泥拓本册中有戴熙(字醇士)跋,云“都之金石友皆曰‘印模’,熙以为模必四匡高起,此不高也,非模,当是汉人搏土用印,有所附洒以为符验之物,所谓印泥。今人以朱为之,钤信札书画者,名之曰泥,其实非泥,盖袭其名耳”。童衍方:《释六舟旧藏汉封泥拓本册概述》,《西泠印社》2008年8月版(总第18期),第37页。
[15] 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山东省图书馆1925年版,扶桑社《封泥大观》平成十九年(2007年)影印版,第152页。
[16] 罗振玉:《郑盦封泥序》,《贞松老人外集》卷一,《松翁近稿(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788页。
[17] 罗振玉:《雪堂藏古器物目录》,《雪堂藏古器物目录(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1—81页。
[18] 周晓陆:《“泥封”“封泥”称谓辨》,《西泠艺从》2019第12期,第5—8页。
[19] (清)刘鹗:《铁云藏陶》,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影印本,第97—98页。
[20] 此数据从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影印本统计。孙慰祖在《古封泥集成》中指出,“《铁云藏封泥》,初辑成当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录入114枚,后于1904年附入《铁云藏陶》印行。”
[21] (清)陈介琪:《十钟山房印举·封泥》,光绪九年(1883年)刊,扶桑社《封泥大观》平成十九年(2007年)影印版。
[22] (清)吴式芬、陈介琪:《封泥考略》,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影印版。
[23] (清)吴式芬、陈介琪:《封泥考略》,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影印版,第140—141页。
[24] 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年版,第26页。
[25] 胡平生:《简牍检署考导言》,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6] 孙慰祖:《古封泥集成》序《古封泥述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27]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上编,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28] 王辉:《秦封泥的发现与研究》,《文物世界》2002年第2期,第26—29页。该文后转载于《大匠之门5》,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181页。《古封泥的发现、著录与研究概况》,《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4辑,三秦出版社第2017年版,第112—121页。
[29] 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6页。
[30] 杨广泰:《秦官印封泥著录史略》,《金石》第一辑,第64—79页。
[31] 郑宇清:《〈封泥考略〉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3月版。
[32] 吕健:《汉代封泥的考古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33] 郑宇清指出,《长安获古编》所辑封泥数量应为29枚(另有1枚泥印)见郑宇清《〈封泥考略〉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264页。
[34] 学者多记该书封泥为114枚,郑宇清核算后指出,其所辑封泥为165枚,见郑宇清《〈封泥考略〉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265页。认为114枚是误算,无关版本。但二数字差异过大,推测应有其它原因。
[35] 该书著录封泥的数量说法不一。郑宇清核算后指出,《封泥考略》所辑封泥数量为843枚(另有3枚泥印)见郑宇清《〈封泥考略〉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268页。
[36] 学者对该书著录封泥数说法不一。郑宇清核算后指出,《再续封泥考略》所辑封泥数量当为320枚(删去两枚与《封泥考略》重见者),见郑宇清《〈封泥考略〉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268页。
[37] 目前学者对该书著录封泥数量多为464枚,郑宇清在核算后指出,其所辑封泥数量当为465枚,见郑宇清《〈封泥考略〉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267页。
[38] 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大业印刷局1940年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7—193页。
[39] 东亚考古学会:《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汉以前遗迹》,东亚考古学会1931年版,插图二六。
[40] 王绵厚、郭守信:《辽海印信图录》,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该书称两封泥在“解放后出土于旅顺口区铁山镇刁家村南牧羊城址”。从其发布的拓片看,与日人《牧羊城》所发掘的封泥照片完全一致,但与其所发布的封泥照有较明显差异,不排除在解放后另有出土的可能性。
[41] (清)吳大瀓藏并撰:《愙齋所藏封泥目》,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42] 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山东省图书馆1925年,扶桑社《封泥大观》平成十九年(2007年)影印版,133页。
[43] 孙慰祖:《古封泥集成》之《古封泥述略》,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44]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上编《秦封泥简论》,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45] 郑宇清:《〈封泥考略〉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年3月版,第160页。
[46]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一九五四年秋季洛阳西郊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5期,第27—28页。
[4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4页。
[4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第230页。李恭笃:《凌源安杖子古城出土一批西汉封泥》,《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第2期。又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49] 王绵厚、郭守信:《辽海印信图录》,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7—13页。
[50] 冯永谦、姜念恩:《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第159—161页。
[51] 古陶文明博物馆:《圆梦之旅——一个博物馆人的逐梦旅程》,古陶文明博物馆2015年版,第150页。
[52] 周晓陆:《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与初步研究》,《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331页。
[53] 孙慰祖:《新见秦官印封泥考略》,《大公报·艺林》1996年7月12日。该文后收入《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1999年版。
[54] 王辉:《古封泥的发现、著录与研究概况》,《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4辑,三秦出版社第2017年版,第113页。
[55] 孙慰祖:《古封泥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56] 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3页。
[57] 古陶文明博物馆:《圆梦之旅——一个博物馆人的逐梦旅程》,古陶文明博物馆2015年版,第226页。
[58] 吴振烽:《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封泥》(上、下),《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第49—59页;第6期第53—61页。
[59] 古陶文明博物馆:《圆梦之旅——一个博物馆人的逐梦旅程》,古陶文明博物馆2015年版,第163页。
[60] 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第35—49页。
[61] 张翔宇:《相家巷秦封泥的发现与整理》,《美术报》2019年3月2日第10版。王辉:《古封泥的发现、著录与研究概况》,《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4辑,三秦出版社第2017年版,第113页。
[62] 倪志俊:《空前的考古发现丰富的瑰宝收藏——记西安北郊出土封泥出土地点的发现及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新如此的大批封泥精品》,《书法报》1997年4月9日。
[63] 罗小红:《秦封泥的重大发现》,《说古道今》1997年第2期。
[64] 傅嘉仪、罗小红:《汉长安城新出土秦封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封泥初探》,《收藏》1997年第6期,第7—8页。傅嘉仪《秦封泥欣赏》,《收藏》1997年第6期,彩页。
[65] 《西安北郊新出土封泥选拓》,《书法报》1997年4月9日第4版。任隆:《秦封泥官印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第17—35页。
[66] 崎岖:《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简介》,《终南》第1辑,1997年10月,第17—23页、封底。
[67] 周晓陆、路东之、庞睿:《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第50—59、77页。
[68] 任隆:《秦封泥官印续考》,《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8年第3期,第22—14页。
[69] 古陶文明博物馆:《道在瓦砾——一个博物馆人的逐梦旅程》,古陶文明博物馆2015年版,第163页。
[70] 古陶文明博物馆:《圆梦之旅——一个博物馆人的逐梦旅程》,古陶文明博物馆2015年版,第163页。
[71] 傅嘉仪:《篆字印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72] 孙慰祖:《新发现的秦汉官印、封泥资料汇释》,《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7页。
[73] 傅嘉仪:《历代印匋封泥印风》,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67页。
[74]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509—544页。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第427—452页。王伟在整理后指出,《发掘·出土封泥统计表》中列出全部325枚封泥。其中T2③∶70、TG1∶5、TG1∶77三枚是无字封泥;另有T2③∶89、T2③∶168、T2③∶170、T2③∶171、T2③∶172、T2③∶173、T2③∶180、T3③∶38、TG1③∶81九枚“文字漫漶”。除去3枚无字封泥和9枚“文字漫漶”者,《发掘·出土封泥统计表》共公布了185种,313枚封泥的资料(包括残字封泥在内)。
[76] 杨广泰:《秦官印封泥聚》,文雅堂2000年版。是书未见,转引自周晓陆《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与初步研究》,《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页。
[77] 王辉:《秦印考释三则》,《中国古玺印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版。
[78] 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
[79] 肖春源:《珍秦斋藏印·秦印篇》澳门文化厅2000年版。
[80] 周晓陆、刘瑞:《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1年第4期。
[81] 许雄志:《秦印文字汇编》,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82] 傅嘉仪:《西安新发现秦封泥》,《书法》2001年第10期。王辉:《秦印封泥考释(五十则)》,《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文物》2001年第12期。
[83] 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续》,《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八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王辉:《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文物》2001年第12期。
[84] 周晓陆、陈晓捷:《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秦文化论丛》第九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5] 周晓陆等:《秦封泥再读》,《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86] 傅嘉仪:《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西泠印社2002年版。
[87] 刘庆柱:《新获汉长安城遗址出土封泥研究》,(《石璋如先生百年寿诞纪念文集——考古·历史·文化》,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版。
[88] 周晓陆、陈晓捷:《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印》,《秦文化论丛》第9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9] 周天游、刘瑞:《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简读》,《文史》2002年第3期。
[90] 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180、220页。
[92] 王辉:《释秦封泥中的三个地名》,《秦文化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93] 路东之:《问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掇英》,紫荆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
[94] 徐畅:《中国书法全集·先秦玺印》,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版。
[95] 平出秀俊:《新出相家巷秦封泥》,艺文书院2004年版。
[96] 伏海翔:《陕西新出土古代玺印》,上海书店2005年版。
[97] 周晓陆、陈晓捷、汤超、李凯:《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周晓陆、刘瑞、李凯、汤超:《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5期。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碑林集刊》第1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98] 马骥:《西安新见秦封泥及其断代探讨》,《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7日。
[99] 马骥:《西安近年封泥出土地调查》,《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2010年版,第30页。
[100] 陈晓捷、周晓陆:《新见秦封泥五十例考略——为秦封泥发现十周年而作》,《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6年第2期。
[101] 李晓峰、杨冬梅:《济南市博物馆藏界格封泥考释》,《中国书画》2007年第4期。
[102] 傅嘉仪:《秦封泥汇考》,上海书店2007年版。
[103] 路东之:《问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馆藏品掇英》,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
[104] 王玉清、傅春喜:《新出汝阳郡秦汉封泥集》,上海书店2009年版。
[105] 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中华书局2010年版。
[106] 郭富纯:《大连古代文明图说》,文史出版社2010年6月版。
[107] 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新出战国秦汉封泥特展图录》,西泠印社2010年版。
[108] 杨广泰:《新出封泥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
[109] 许雄志:《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河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
[110] 周晓陆:《酒余亭陶泥合刊》,艺文书院2012年版。
[111]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藏秦封泥图录》,《唐都学刊》2012年第6期。
[112] 陈晓捷、周晓陆:《文雅堂藏秦封泥选考》,《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13] 王辉:《秦陵博物院藏汉封泥汇释》,《秦始皇陵博物院》2015年总五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14] 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15] 王辉、王巧英:《释文雅堂藏几枚与府有关的秦封泥》,《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1辑,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
[116] 王伟:《文雅堂藏新品秦封泥考释(二十则)》,《中国文字研究》第2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117] 西泠印社美术馆:《古代封泥精品展》,文雅堂2015年版。
[118] 杨广泰:《新出陶文封泥选编》,文雅堂2015年版。
[119] 庞任隆:《秦封泥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
[120] 蔡庆良、张志光:《秦业流风:秦文化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6年版。
[121] 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中西书局2016年版。
[122] 王伟:《新见秦地名封泥选释(十五则)》,《出土文献》第10辑,中西书局2017年版。
[123] 魏杰:《冰斋魏杰藏秦封泥》,《金石研究》第1辑,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36—141页。
[124]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秦封泥选》,《书法》2017年10期彩版。
[125] 许静洪、许云华:《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藏玺印封泥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年版。
[126] 李振洲:《中国文字博物馆馆藏秦代封泥鉴赏》,《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12期。
[127] 任红雨:《中国封泥大系》,西泠印社2018年版。
[128] 许卫红、张杨力铮、赵震、狄明:《陕西省咸阳城府库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9年5月8日8版。
[129] 孙慰祖:《新出封泥撷珍》,《问印》第一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第131—135页。
[130] 许雄志:《鉴印山房藏古封泥选粹》,鉴印山房金石文存2019年版。
[131] 李超:《秦封泥与封简制度》,《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第86页注6。
[132]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的发现与研究》,《周秦汉唐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133] 周晓陆:《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与初步研究》,《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4] 王辉:《秦封泥的发现及其研究》,《文物世界》2002年第2期。
[135] 王辉:《古封泥的发现、著录与研究概况》,《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4辑,三秦出版社第2017年版。
[136] 刘瑞:《1997——2001年秦封泥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9期。
[137] 刘瑞:《1997—2002年间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研究综述》,《秦文化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138] 阿敏:《考古重大发现,印苑别开生面——记《秦封泥集》问世》,《中国书法》2001年第5期。
[139] 崔璨:《近十年来秦封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泠艺从》2019年第12期,第15—20页。
[140] 王伟在多年前已指出,其了解到而未见原书的,至少有北京文雅堂出版的《秦官印封泥聚》(原拓,两册,89种89品)、《原拓新岀土秦封泥》(一函十二册,收录秦封泥261种648品,2003年)、《双圣轩集拓秦官印封泥》(收录100枚)、《相家巷出土秦封泥》(一函十四册,收录秦封泥403种,764品。近年任红雨编辑出版《中国封泥大系》的大成功,即是其对自己收藏的大量原拓的充分使用。直到2019年秋,我们依然可以在网络上购买到《西安出土秦封泥》原拓,其中尚有不少封泥在之前未见刊布,但藏家不详。
[141] 施谢捷:《谈〈秦封泥汇考〉〈秦封泥集〉中的同一封泥重复著录问题》,《西泠艺从》2019年第12期,第2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