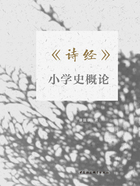
前言
《诗经》小学类属于实践性很强的传统语文学,它是在《诗经》阐释过程中产生的一切与小学紧密关联的学术活动及学术成果。研究和总结《诗经》小学成果,对于准确解释《诗经》之蕴意,继承和弘扬《诗经》文化意义重大,夏传才先生说:“我们认为两千年积累的《诗经》研究资料极为丰富,训诂、名物考证、音韵、校勘都有积极的成果,如果离开这些资料,《诗经》在现代人面前只是一串串不可理解的文字符号。”[1]《诗经》小学史的主要任务,是从小学的角度观察《诗经》阐释的历史,也就是以传统语文学发生、发展的角度对历史上的《诗经》解释现象进行全方位的考察,重点在于呈现《诗经》小学活动的基本面貌和历史规律。
《诗经》阐释是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产生于经学传播实践中,并且对经学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当社会形态跨入近现代社会门槛后,经学因无法适应社会进步而逐渐瓦解,传统小学却因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而逐渐融入当代文献语言学,它与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的关系都十分紧密,却不能与其中的任何学科或几个学科的组合画上等号。
一 文字训诂与《诗经》小学
“小学”最早是指初级教育机构,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2]“六书”乃文字声音义理之汇总,掌握“六书”理论能够快速提升低龄学习者的识字效率和用字能力。西汉刘歆在《七略》中最早把识字课本性质的《史籀篇》《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等列在《六艺略》的小学类别之中。直到《旧唐书·经籍志》的出现,有训诂书鼻祖之称的《尔雅》才第一次被纳入小学之类。
可是,如果从学科性质上来看,与小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却是训诂学。训诂学之名最早见于汉代的《毛诗故训传》(亦称《毛诗训诂传》[3],简称《毛传》),但若从训诂实践上来看,可以说它最早萌芽于重视文献事业的西周时期,《礼记·学记第十八》:“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礼记集解》云:“郑氏曰:比年入学,学者每岁来入学也。中犹间也。间岁则考学者之德行道艺。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志意所趣向也。……张子曰:离经,辨析经之章句也。事师而至于亲敬,则学之篇而信其道也。”[4]无疑,“离经”“辨志”须臾也离不开训诂的功夫。
在训诂方面,《诗经》训诂实践很早就被文献记载了下来。据《国语·周语下》记载,晋国大夫叔向前往东周朝聘,时任王室卿士的单靖公礼数备至地宴请了他,席间谈及了《昊天有成命》这首诗。朝聘活动结束,单靖公亲送叔向至城郊而返,由家臣继续送他返回晋国。叔向向这个家臣详细讲解了《昊天有成命》,其间有字词训诂,有串讲大意,有诗旨归纳,最后联系现实,推阐微言大义,称赞单子之德曰:“单子俭敬让咨,以应成德。单若不兴,子孙必蕃,后世不忘。”大意为:“单子俭朴、恭敬、礼让、善问,可以担当‘成’之美德。单子如果不能振兴周王室,他的子孙一定会兴旺发达,后世不会忘记他。”[5]这则记载可以视作《毛传》的源头。
二 音韵学与《诗经》小学
关于语音探索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老子·第二十章》云:“唯之与阿,相去几何?”有当代学者注释道:“唯,应诺之声,古书回答时常有‘唯唯’。阿,同‘诃’,呵斥、责备之声。成玄英云:‘唯,敬诺也。阿,慢应也。’”[6]上古音中,“唯”为喻母微部,“阿”为影母歌部,二者读音较为接近。《管子·小问》记载,齐桓公与管仲讨论攻打莒国的时候,东郭邮遥望他们开口而不闭,就猜到了他们讲的是“莒”,因为“莒”在上古为见母鱼部,发音须长时间保持开口状态。《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云:“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乃难乎而也。”何休注:“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7]上古音中,“而”为日母之部,“乃”为泥母之部,二者在声母的发音特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在韵母的洪细方面略有不同。《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云:“《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8]两个“伐”以字调的舒促来区别词义。
东汉以来,由于当代语音跟先秦语音差别越来越大,逐渐引起某些学者的注意。《豳风·东山》云:“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毛诗传笺》(以下简称《郑笺》):“古者声栗、裂同也。”《小雅·常棣》云:“常棣之华,鄂不
 。”《郑笺》:“不,当作拊。拊,鄂足也。……古声不、拊同。”《小雅·常棣》又云:“每有良朋,烝也无戎。”《毛传》:“烝,填。”《郑笺》:“古声填、窴、尘同。”刘熙《释名·释车》云:“车,古者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车,舍也,行者所处若居舍也。”[9]但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注音方法主要是直音法和譬况法,无法更进一步区别读音方面的细微差别。
。”《郑笺》:“不,当作拊。拊,鄂足也。……古声不、拊同。”《小雅·常棣》又云:“每有良朋,烝也无戎。”《毛传》:“烝,填。”《郑笺》:“古声填、窴、尘同。”刘熙《释名·释车》云:“车,古者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车,舍也,行者所处若居舍也。”[9]但是,由于那个时代的注音方法主要是直音法和譬况法,无法更进一步区别读音方面的细微差别。
东汉末年,由于受到梵语的启发,学者乃知从声韵两个方面分析语音,于是发明了反切法。《颜氏家训·音辞》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10]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寻颜师古注《汉书》,引服虔、应劭反语不下十数事,服、应皆卒于建安中,与郑玄同时。是汉末已行反语,大体与颜氏所述相符。至谓创自叔然,殆非情实。”[11]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说:“颜之推所说的‘汉末人独知反语’的话是可靠的,但是不要归功于孙炎一个人,而应该是时代造成的。”[12]反切法流行开来以后,各种音义之作大量产生,《颜氏家训·音辞》谓“自兹厥后,音韵锋出”。音义体的《诗经》小学代表作品主要有徐邈的《毛诗音》、陆德明的《毛诗音义》等。
六朝经师在给《诗经》作注时,遇到失韵的地方,往往以“取韵”或“协句”为标志临时改变韵脚字的读音,以便吟咏或唱诵。陆德明认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13],但他在《经典释文》中还是以“协韵”或“协句”为标志引用了徐邈和沈重等人的协音材料。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李贤注《后汉书》、李善注《文选》,亦用协读音之法。颜师古在《汉书注》中以“合韵”标注了不少的协读音,在《匡谬正俗》和《急就篇注》中亦论及了古音问题,如他在《急就篇注》“竺谏朝”条目下注曰:“以‘朝’韵‘吾’者,古有此音,盖相通也。班固《幽通赋》曰:‘巨滔天而泯夏,考遘愍以行谣。终保己而贻则,里上仁之所庐。’类此甚多,不可具载。”[14]受协韵音释的启发,南宋吴棫开始考释古音,“吴棫著《诗补音》,实际上是在《诗经》用韵的前提下,将汉魏六朝及隋唐以来诸家音义一一考究,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15]明末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彻底否定叶音说,为《诗经》的韵脚字构拟了古音。清初顾炎武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第一次构建了古韵系统,初步掌握了古今语音分合的规律。戴震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其阴阳对转理论影响甚巨,王国维《五声说》云:“尝谓自明以来,古韵学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古本音不同今韵之说,二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三为段氏古四声不同今韵之说。而部目之分析其小者也。”[16]戴震对于《诗经》小学影响更大的地方,还在于他把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的研究融为一体,运用古音学研究成果来考释经籍文字,与他的两大高足段玉裁、王念孙一起引领了乾嘉小学的潮流。
三 文献学与《诗经》小学
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诗经》的整理历史悠久,《国语·鲁语下》记载,鲁国大夫闵马父谓景伯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17]孔颖达《毛诗正义》云:“然则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师校之也。”[18]指出正考父为周宣王时宋国的大夫,孔子的七世祖,由他最早校订了《诗经·商颂》诸篇,“这便是我国历史上从事校书的开端”。[19]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的《诗经》有三千多首诗,孔子删去重复和不合礼义的篇章,只留下三百余首。孔子整理过《诗经》,但他的诗教活动主要是以口耳相授方式进行的,文本用字问题并非其关注焦点。战国时,“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叙》),《诗经》用字较为混乱。战国晚期,荀子提出语言规范问题,他在《正名》篇中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20]李斯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同书文字”,在一定程度上践履了他的老师荀子的“正名”理想。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加上秦末战乱,经籍旧文竟一度几于断绝。
汉立,惠帝废“挟书令”,文、景开献书之路,广搜经籍,而《诗经》仅赖口传得以用汉代古隶抄写成册,形成齐、鲁、韩三家诗,并先后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毛诗》晚出,《汉书·艺文志》:“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21]孔颖达曰:“《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22]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所得书皆先秦旧书,因为《毛传》保留了不少先秦儒学的内容,在思想上又有明显的复古倾向,故而深得他的青睐,从而打上了古文经学的烙印。西汉末年,极好古文的刘歆深得哀帝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汉书·楚元王传》),终未能遂愿。王莽改制,欲利用古文经学树立新的思想权威,遂建立了《毛诗》博士。新莽政权失败后,《毛诗》的官学地位旋即被废。四家诗学术旨趣不同,文本互异,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自叙》云:“其始口相传授,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各用其乡音。故有同言而异字、同字而异音者。”[23]古文经学家许慎撰有《五经异义》,熟知五经异同,但因《毛诗》多假借,故而他在《说文解字》中屡引今文三家诗以证文字之本义。汉末郑玄先学今文,后通古学,笺注《诗经》时以《毛诗》为本,校勘以今文三家诗及其他典籍,段玉裁赞之曰:“而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氏者也。”[24]唐代一统四方,颜师古受命参照《说文解字》《字林》《玉篇》等字书及前代石经拓本确定各经楷书文字,《旧唐书·颜师古传》云:“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服。”[25]书成,颁行天下,号称定本,此亦为《毛诗正义》文字的主要渊源。
四 《诗经》小学的综合性和独特性
《诗经》小学纵贯传统经学发展的始终,并在现代学术体系下成功蜕变为几种新学科的重要内容,这说明它具有极强的学科综合性和学术生命力,甚至在某个历史阶段或某个学科方向上持续展现出强大的学术引领力量。比如在音韵学研究领域,与《诗经》相关的古今著作就有徐邈《毛诗音》、沈重《毛诗音》、陆德明《毛诗音义》、吴棫《诗补音》、陈第《毛诗古音考》、顾炎武《诗本音》、段玉裁《诗经韵谱》、王力《诗经韵读》、王显《诗经韵谱》等,可以说对《诗经》韵字的审视一直都是古音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在《诗经》小学文献梳理研究的过程中,首先要着眼于经学发展大局,因为传统经学的发展是直接推动《诗经》小学发展的恒久力量。其次,要考虑中国历史上的部分强势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给《诗经》小学发展带来的冲击,围绕特定的文化因素检视《诗经》小学成就,方能准确把握《诗经》小学的发展方向,表述起来也才能做到有条不紊。在先秦时期,孔门诸儒是《诗经》学的核心力量,有赖于他们的持续努力,在原始宗教文化、西周礼乐文化环境中积淀而成的朴素诗作,演变成为高居庙堂的经学权威。在两汉,古文经学家和小学家崇尚真理,不嫌细碎,严谨为学,埋首著述,淘汰并超越充满神秘、媚上色彩的今文三家诗,《诗经》小学从此走进广大士子的读书生涯。南北朝时期,音韵学锋出。有唐一代,字样学盛行,《诗经》小学也随之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宋人厌旧而求新求奇,范仲淹、欧阳修革故立新在先,王安石《诗经新义》及《字说》嗣后开拓新局,后有朱子《诗集传》融理学于《诗经》学,影响宋、元、明三代。清代朴学大盛,《诗经》研究局面为之一新,先有陈启源高举稽古大旗,续有乾嘉学派构建《诗经》小学理论体系,终有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的三种新疏代表。
跟普通的语言文字考释进行比较,很容易发现《诗经》小学的另一特色。黄侃先生将训诂分为“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他说:“小学家之训诂与经学家之训诂不同。盖小学家之说字,往往将一切义包括无遗。而经学家之解文,则只能取字义中之一部分。……是知小学之训诂贵圆,而经学之训诂贵专。经学训诂虽有时亦取其通,必须依师说展转求通,不可因猝难明晓,而辄以形声相通假之说率为改易也。”[26]小学考释可以因字义系联而触类旁通,经学训诂则必须同时考虑上下文的语意贯通。高邮王氏父子精于小学,然有时亦有疏于经学之弊,陈澧《东塾读书记》云:“王怀祖《广雅疏证》尤精于声音训诂,然好执《广雅》以说经。如‘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毛传》云:‘僮僮,竦敬也。祁祁,舒迟也。’诗意言祭时竦敬,去时舒迟,而借被以言之,《毛传》深得其意。王氏《经义述闻》,据《广雅》‘童童,盛也’,因谓‘祁祁’亦盛貌,则失诗意矣。由偏执《广雅》故也。”[27]
[1]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增注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2] (汉)许慎撰,陶生魁点校:《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92页。
[3] 周信炎:《训诂学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4]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59页。
[5] 陈桐生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6页。
[6] 汤漳平、王朝华译注:《老子》,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7页。
[7]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1页。
[8]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41页。
[9] (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6—247页。
[10] 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8页。
[11] (唐)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张力伟点校:《经典释文序录疏证:附经籍旧音二种》,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9页。
[12]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7页。
[13] (唐)陆德明撰,张一弓点校:《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14] 管振邦:《颜注急就篇译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15] 张民权:《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16] 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17] 陈桐生译注:《国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1页。
[18]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0页。
[19]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20] 方勇、李波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58页。
[21]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56页。
[22]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3] (清)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续修四库全书》第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页。
[24] (清)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2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52页。
[26]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27] (清)陈澧著,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