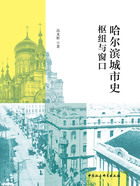
序言
哈尔滨是生养我的故乡,我对她的爱恋随年龄增长而增长,随离乡三十余年而愈发浓烈。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说过:“爱国应该和爱自己家乡一样。”俄罗斯人文大家利哈乔夫(Д.С.Лиxачёв,1901—1999)也说过:“事实上,爱国首先要从爱自己的城市、爱自己的家乡开始。”(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патриотизм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любви к своему городу,к своей местности.)作为以世界史,尤其是俄国史研究为志业的学者,我是从对故乡的体认开始了对周边世界的认识。哈尔滨这个中国史、中外关系史和世界史的典型案例,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给了我无尽的灵感和启迪。我一直设想用自己毕生的学术功力为故乡——哈尔滨写一部“大书”,但终觉积累不足而未果,而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高龙彬君的皇皇专著弥补了我的遗憾。作为高龙彬君的老师,我首先对他表示祝贺,其次想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
当代著名史学家戴逸这样评价中国东北的地理区位、历史影响和学术价值:“它所处地理位置独特,与中原相距最近,地域辽阔,南北贯通,无门庭之限,生态资源丰富,可耕可牧可猎可渔。这里,自古就是游牧、渔猎和农耕诸民族世代生息家园,相互角逐的舞台。东北地区的肥土沃野,培育出一代代强族,不断崛起,雄飞中原,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先后占有北方半壁,或一统天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北长久地处于战略地位,不断给中原王朝注入强大的影响,甚至决定其盛衰或兴亡。”[1]
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对中国“三北”(东北—华北—西北)考察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更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为中国东北是世界“风暴中心”(storm center) [2],即地缘政治理论奠基人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论说中的“历史地理枢纽”(Geographical Hub of History)。拉铁摩尔于1929—1930年用了9个月游历东北全境,他在《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满洲的小道与偏远地区》(Byroads and Backwoods of Manchuria)等著作中预言“在这种争夺当中,那些将帅和政治家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传统、生活、种族和各个地域在面对各种文化与民族时维护自身的努力,以及民族和文化将他们自身强加到各个种族和地域之上的努力,这才是历史真正的本身。”[3]
然而,反观中国知识界对于东北史地的研究却是严重不足。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傅斯年在1931年就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人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著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诸?”[4]1931年10月,傅斯年联合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和蒋廷黻等著名史学家编写了《东北史纲》。
金毓黻在其《东北通史》中亦强调:“今日之东北,已等于黑龙江迤北乌苏里江迤东之地,沦于外人,非复我有,吾人悼心失图,唤起重大之注意,尤非昔比是也。尽往日之东北,为我国土之一部,与内地其他各省等,搜辑其佚事旧闻,撰为方志,或地方史,合而为一部述之,固可,分而为数部述之,亦无不可。今则举其全区,同归沦陷,势非合而述之,为一整个之地方史,将无以详其原委,明其因果。”“不知此义,而犹以旧见自缚,则东北一词,不过为强者割据自雄之资,所新造之东北史,不过为国别史一种,而与所受之外祸固无与,且非所以语于今日之东北也。此为今日讲东北史最要之义,有心之士,其可忽诸。”[5]
因此从东北史学科创立之初,即把“东北”作为一个不同于中原地区“十里不同俗”“相邻不能语”的整体统一的区域看待,在论及政权沿革、经济活动、种族民族和对外关系时,较多地从东北整体来考虑。因此,东北史自其创立之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后世所称的“区域史”和“大历史”特色。
而位居北疆中心位置的哈尔滨正因为具有居中心—边缘之要冲、内陆—外省之核心、水—陆交通之枢纽、文化—文明之多元、民族—种族之融合、本土—境外之交会的鲜明特质,实际上正处于拉铁摩尔笔下“风暴中心”的“风暴眼”(eye of the storm)的位置,其自然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国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学术价值更是自不待言的。
城市作为一种地域现象、一种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和实现场所,随着社会学、地理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城市史研究应运而生,而城市史框架下的哈尔滨史则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受国际和本国形势的影响,大量的国外移民从苏(俄)、日本、朝鲜和欧美等国或移居我国东北地区,或自东北地区移住其他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外国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并未将东北当作“异乡”,哈尔滨就曾一度被在哈尔滨的俄侨视为自己的“首都”和“第二故乡”,其城市建筑、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化等都留下了俄侨印迹,俄侨史推动了哈尔滨等极具特色的东北城市历史的研究。正如石方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中所述,“过去论者把帝俄以中东铁路为媒介,对我国东北实行军事上占领、政治上侵略、经济上掠夺、文化上渗透均有述及,道出了‘侵略的西方’的本质。但仅限于此就不够全面了,除了要讲‘侵略的西方’的本质外,还要看到中东铁路亦是西方精神与物质文明传播的媒介,客观上起着开风气之先河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行的作用,由此展现出‘文明的西方’的另一面。中东铁路的修筑,完全改变了哈尔滨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强力之下,以硬性移植和强迫过渡为特征开始了其痛苦尤烈的社会文明转型”[6]。
如果将哈尔滨城市历史置于欧亚广阔但势力逼仄的空间视野下进行考量,研究者不仅可以看到哈尔滨在东北历史和地理中的分量,也可以看到哈尔滨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哈尔滨城市史出发,以研究东亚史、世界史乃至全球史的视角,帮助我们认识世界。
1987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是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她提出:“历史研究需要建立坚强的跨学科联系,以提供新的资料来源或有关因素(如气候和土壤),或提供历史学家不熟悉的解释方式。”[7]如果说20世纪初叶是中国现代史学的确立期,并且奠定了中国东北史(包括哈尔滨史)的研究使命的话,21世纪初叶则是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转型期,而哈尔滨城市史的研究同样面临重大调整的新使命。历史研究的目的逐渐由为执政者“资治”转为解决现实问题,因而史学研究更强调社会进步和变化的观点,并且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治史”。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与现实紧密相关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因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甚至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逐渐运用到传统的哈尔滨城市史的研究之中。近年来,应用多角度研究哈尔滨城市史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无论是传统的地方史、边疆史还是新兴的区域史、全球史,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史、民族史、外交史、文化史还是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新冷战史,都应该成为哈尔滨城市史可资借鉴的方法。
高龙彬君深受历史学基础和史学理论的厚重滋养,他在“回炉”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曾以专业记者之眼观察并体识他的第二故乡——哈尔滨达五年之久,感性认识与理性之思的叠加促成了他对哈尔滨城市史的浓厚兴趣,而世界史专业、俄国史方向和新史学理论的素养加持了他对哈尔滨城市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作为哈尔滨人和高龙彬君的老师,我对他的哈尔滨城市史的研究寄托了极大的期冀。希望他在个人兴趣与史学使命之间、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在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之间找到立身和立言之道,希望他为我的故乡和他的第二故乡贡献智慧和才华。
是为序。

2022年6月6日普希金诞辰日暨国际俄语日
[1] 戴逸:《清代黑龙江将军与东北边疆治理》,载《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
[2] Owen Lattimore,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32,p.4.
[3] Owen Lattimore,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32,p.301.
[4] 傅斯年:《东北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5] 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6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翻印,第50页。
[6] 石方:《20世纪一二十年代哈尔滨多元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7] 《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8—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