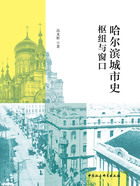
自序
哈尔滨是一座文化多元、交互与共生的城市,华洋杂处,中西交融。
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1897年贯穿中国东北的东清铁路(1920年后改称中东铁路)开工建设,1903年东清铁路全线通车。随着东清铁路的建设与开通,哈尔滨迅速从一个自然经济状态的渔村发展成一个近代化与国际化的大都市,成为“东西文明的交界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与东亚的中心,曾经有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民族或族群的人生活在哈尔滨,十几个国家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或代办处。哈尔滨的近代化是“后发型”的典型。哈尔滨曾经是东清铁路的“附属地”,日本的殖民地,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苏联的援助地,东北老工业基地、东北全面振兴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
哈尔滨城史纪元是哈尔滨城市史研究的一个关键性和节点性问题,千年文脉的“金源说”,以金朝建国为起点;百年设治的“设治说”,以滨江关道设治为起始;建设周年的“铁路说”,以中东铁路的开工或开通为肇始。哈尔滨是一个“依水而定,因路而兴”的城市,东清铁路因松花江形成的特殊区域而选定哈尔滨作为铁路枢纽。哈尔滨地名及其来源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满语、蒙古语、女真语和俄语等各有说辞,目前学者基本取向是满语。满语、汉语、俄语与日语等不同语种的与哈尔滨相关的地图,是考证哈尔滨一些地名的重要资料载体。
在百余年中,哈尔滨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次转型与三次高峰,从传统农业聚落到近代新兴城市、从铁路“附属地”到独立自主、从现代工业主导到区域多元成长。“闯关东”不仅是一部“逃荒史”,也是一部“淘金史”。湖北的理发业、宁波的裁缝业(红帮)、扬州的洗浴业、山东和河北的传统曲艺等文化,融合生成了哈尔滨别具特色的市井生活。“功成玉钱庄”是山东“闯关东”的“五大功”商号的重要支柱产业,是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资本发展的缩影。哈尔滨还有山东的张廷阁、河北的武百祥等“闯关东”的民族资本产业,“双合盛”“同记”与“大罗新”等曾经闻名于世。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往往是单体的呈现,区域间互动和比较研究是一个可以拓展的学术领域。哈尔滨与天津、上海、青岛等地的经济文化联系需要深入研究。
哈尔滨是一个曾经侨民比中国人数量多的城市。俄国、波兰、立陶宛、美国、法国、英国、丹麦与意大利等国家的人在哈尔滨生活工作,犹太人、卡拉伊姆人、高加索人与塞尔维亚人等在哈尔滨从事各种行业。犹太人在哈尔滨建立社区,修建教堂和墓地,组织和建立犹太宗教公会、犹太丧葬互助委员会、犹太公共图书馆、犹太医院与犹太学校等机构,以中央大街为中心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哈尔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哈尔滨基督教卫斯理会等都曾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的重要场所,是隐蔽战线中的重要记忆。波兰人与立陶宛人在哈尔滨的人口变迁,见证了哈尔滨外国侨民的历史演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法国(欧洲、德国)、日本与俄国三条路径。作为东清铁路的枢纽,哈尔滨是这三条路径的交会点,不仅有理论的传播,还有实践的传播。哈尔滨是我国最早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城市,亦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最早成立组织的城市。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哈尔滨具备与上海、北京等地同样的重要地位。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楚图南、侯外庐等都在哈尔滨留下了革命和学术的足迹。哈尔滨与北京、上海的“内联”关系,哈尔滨与满洲里、绥芬河的“外联”关系,整体性和系统性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宏大叙事。
包括哈尔滨在内的东北城市文化不同于关内一些地区的单一文化形态。研究哈尔滨城市史需要俄语、日语等外文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利用。《哈尔滨城市史:枢纽与窗口》虽然利用了部分外文资料,但也仅仅是冰山一角。档案是中外学者对话的第一支撑。哈尔滨城市史研究需要包括档案在内的大量原始资料的挖掘和使用。哈尔滨城市史研究是一项交叉和跨学科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的运用,影视史学、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等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拓展。哈尔滨城市史研究不仅是一项区域史或地方史的研究,也是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哈尔滨城市史研究需要国际视野、微观研究、价值判断与现实关怀。
外来文化是哈尔滨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外来文化呈现多元化;本土文化亦是哈尔滨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哈尔滨本土文化亦具有多元性。外来文化及其特色是哈尔滨研究或宣传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俄侨文化的研究与犹太文化的宣传,然而哈尔滨日本殖民文化或日本侨民文化基本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国内关于哈尔滨的波兰、英国、美国、意大利、立陶宛、塞尔维亚等侨民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哈尔滨城市史研究需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研究并驾齐驱。
哈尔滨城市史研究,相对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青岛、成都、广州等地的历史研究,还相对滞后。哈尔滨城市史研究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使命。一切才刚刚起步……